
乡音姐的美文,又是一幅温馨的画。
我们在乡下时都是点煤油灯。刚开始也是每天精心擦拭那透明的灯罩。可是不出几天,灯罩肯定被打碎。所以大多数时间还是点的没罩子的煤油灯。
后来发现,没罩子要省油得多,就不再买罩子了。
灯光当然要暗很多,不过,在这样的灯光下,读了几年书,眼睛竟然没坏。可能还是白天看绿色的时候多吧。








这星期家里事情多点,今天上来一看,朋友们跟了这么多好文字。请让我一统回复我的朋友们吧:
文章写得不好,我自己明白。只是因为朋友们和我曾经走过相同的历史、用过同样的美孚灯、都感受过老辈人对幼年的我们无限的关爱和期望;在没有水果吃的童年,我们都吃过不是水果的凉薯,所以这两篇小文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谢谢大家!
立立、雪雪你们都是神策学院的高才生,我的文章对你们和大家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很骄傲呵
湘琴妹妹是不是想着这琵琶肉要端给智多星去吃?
毛弟提出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那时候长期在豆大的火苗下学习和看书近视眼少,是不是因为我们吃的是粗粮,现在的孩子吃得太精的缘故?
湖边士:我在湖区读书近一年,知道那湖风半夜里从墙下面的缝下面刮进来的感觉, 如果想端着煤油灯走动,还得双手从下面捧着灯喉进风口才行,不然即使有灯罩也会被风吹没了。
笔院长 现在用洋油的日子成了历史,但是我们却不需要再用煤油灯看书了。所以鼻子眼睛都不要担心被熏得乌漆墨黑了。这个公司好像应该叫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吧。煤油是副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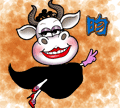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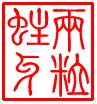







看到照片中的那盏美孚灯,也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也凑热闹给大家讲一个"挑灯夜读"的故事吧:
在那八亿人民八台戏,全国同读一本书的年代,精神食粮比大米更缺乏。想看到一本好小说,真比吃攴肉还难。下放那一阵子,有一次到相邻大队的知青点去串门子,竞然无意中在一位叫齐建平的知青的枕头下摸出一本破旧的书来。这书的书名叫[啼笑因缘],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叫张恨水写的一部言情小说。白话文,章回体,每个章回都有一九字联句的题头。还是繁体竖版的版本。从该书的破旧成度来看,也不知经过多少人之手了。我如获至宝,非借回去看不可,几经软磨硬泡,齐才答应让我看一天。我满口答应,抱着书兴高彩烈地回队去了。
回到家中,匆匆吃完晚饭,就点上一盏煤油灯,用点点网友讲述的那种灭蚊方法将蚊帐中的蚊子消灭,把灯放在床上,将蚊帐的四周全部都捺入草席的下面,让蚊子无缝可钻,才放心地就着那昏黄的灯光,开始了一顿前所未有的精神大攴。未成想,这一打开书页,就一发而不可收。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我已完完全全地沉迷其中,早已不知今夕为何夕了。直到一口气将书的最后一个字看完,端着那盏煤油灯钻出蚊帐,这才发现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老高了。
这事虽然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书中的故事情节也已淡忘,但书中的人物我还依稀记得有:痴情少爷樊家树,天桥卖唱的沈风喜,侠女关秀姑,还有风情万种的何丽娜,特别是那个侠肝义胆的关寿峰老爷子,更是我心中的英雄。
我至今还没搞明白,我当时能一个通宵将这本书看完,到底是这书实在太好看了,还是当时实在太饥不择食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