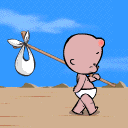冬至日记——报社春秋
——————————
今天是冬至,是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也是数九寒冬的开始——老人最难熬的日子。突然想到该去报社看看父亲生前老友,都八,九十的人,看一回是一回。于是立马叫上老第和一老友,直奔报社。
在报社宿舍23楼6室一厅大套间见到周老,86岁的他坐在轮椅上,头脑已不清醒,认不得人了。现是正厅级待遇。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50年代湖南日报某些政治打手,响应主席号召,将报社60多人打成右派,双开后送往监狱,劳改农场。致使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惨烈残酷是今人不可想像的。如今已全部平反,而当时那些政治打手,却安然无恙,甚至官升三级。见到周老时他还在愤愤不平的念叨着某人的名字。周老是父亲的莫逆之交,四十年代,父亲在报社来稿中,发现周老的投稿,倍感其才,连续登用。以至把他招到报社共事,成为挚友。其时周老已是年青的中共地下党员。57年周老被打成右派,送往监狱关押,直至60年代末才出狱。出狱后听周老聊谈中,说他是从监狱6楼一直改造到一楼才出狱的。原来监狱有规定;改造好的降一楼,直到一楼止。看到周老现住23楼,不免唏嘘和酸楚。周老的儿子周和初,60年代也和我一样,下乡到湘南江永种田,后和初兄历经奋斗,自学成才。现已是长沙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报社右派集团的子女,几乎全部赶下乡,主要下在江永,临湘,沅江等地。后历经磨炼,大都自立成才。报社社长大右派邓均洪老先生虽已过世数年,其子女却个个自学成才,大儿子唐复华60年代下放沅江现已成为文学评论家。三儿子邓晓芒是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60年代下放江永。最有名的是女儿邓小华---残雪女士,如今已是名闻国际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已被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流传。他们都不是科班出身,小华初中都未读完,小芒也只初中毕业,可见他们是何等努力。一时成为报社佳话。
父亲之报社在抗战期间曾聚集过许多文人名士---蒋牧良,艾芜,张天翼,冯雪峰,田汉,等等。他们都为报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成为父亲的挚友,尤其是蒋牧良老先生,老党员,省作协唯一的正军级老作家,鲁迅先生的抬棺人。抗战期间在雪峰山下,蒋老在报社负责编副刊,和父亲结下深厚友情,成为挚友。在父亲打成右派,旁人避之三舍时,他却义无反顾的来看望父亲。全然不睬那些眼色。其女儿蒋子丹从一传达室收发员,成为一知名作家,是离不开蒋老严谨家教的。还有田汉老先生,每到长沙来,都要请父亲去坐坐聊聊,管你老左老右。艾芜,张天翼老先生都是在桂林来到报社的,挤居在报社的几间小屋内,虽很清苦,却还快乐,八十年代在北京再见到张老时,虽然有点胡涂,但还依稀记得报社事。
今天冬至到报社看望原报社活下来仅有的几位老报人,已物是人非,感概万千,但愿历史不再重演,让我们的后人活得轻松些,洒脱些。冬至到了,温暖的春天也即将来临。
——————————
今天是冬至,是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也是数九寒冬的开始——老人最难熬的日子。突然想到该去报社看看父亲生前老友,都八,九十的人,看一回是一回。于是立马叫上老第和一老友,直奔报社。
在报社宿舍23楼6室一厅大套间见到周老,86岁的他坐在轮椅上,头脑已不清醒,认不得人了。现是正厅级待遇。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50年代湖南日报某些政治打手,响应主席号召,将报社60多人打成右派,双开后送往监狱,劳改农场。致使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惨烈残酷是今人不可想像的。如今已全部平反,而当时那些政治打手,却安然无恙,甚至官升三级。见到周老时他还在愤愤不平的念叨着某人的名字。周老是父亲的莫逆之交,四十年代,父亲在报社来稿中,发现周老的投稿,倍感其才,连续登用。以至把他招到报社共事,成为挚友。其时周老已是年青的中共地下党员。57年周老被打成右派,送往监狱关押,直至60年代末才出狱。出狱后听周老聊谈中,说他是从监狱6楼一直改造到一楼才出狱的。原来监狱有规定;改造好的降一楼,直到一楼止。看到周老现住23楼,不免唏嘘和酸楚。周老的儿子周和初,60年代也和我一样,下乡到湘南江永种田,后和初兄历经奋斗,自学成才。现已是长沙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报社右派集团的子女,几乎全部赶下乡,主要下在江永,临湘,沅江等地。后历经磨炼,大都自立成才。报社社长大右派邓均洪老先生虽已过世数年,其子女却个个自学成才,大儿子唐复华60年代下放沅江现已成为文学评论家。三儿子邓晓芒是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60年代下放江永。最有名的是女儿邓小华---残雪女士,如今已是名闻国际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已被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流传。他们都不是科班出身,小华初中都未读完,小芒也只初中毕业,可见他们是何等努力。一时成为报社佳话。
父亲之报社在抗战期间曾聚集过许多文人名士---蒋牧良,艾芜,张天翼,冯雪峰,田汉,等等。他们都为报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成为父亲的挚友,尤其是蒋牧良老先生,老党员,省作协唯一的正军级老作家,鲁迅先生的抬棺人。抗战期间在雪峰山下,蒋老在报社负责编副刊,和父亲结下深厚友情,成为挚友。在父亲打成右派,旁人避之三舍时,他却义无反顾的来看望父亲。全然不睬那些眼色。其女儿蒋子丹从一传达室收发员,成为一知名作家,是离不开蒋老严谨家教的。还有田汉老先生,每到长沙来,都要请父亲去坐坐聊聊,管你老左老右。艾芜,张天翼老先生都是在桂林来到报社的,挤居在报社的几间小屋内,虽很清苦,却还快乐,八十年代在北京再见到张老时,虽然有点胡涂,但还依稀记得报社事。
今天冬至到报社看望原报社活下来仅有的几位老报人,已物是人非,感概万千,但愿历史不再重演,让我们的后人活得轻松些,洒脱些。冬至到了,温暖的春天也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