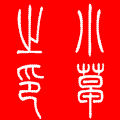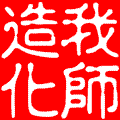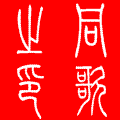邀我们到茅屋湾去的,是原在我家照顾我父母的小卢。我父母七十几岁以后,就一直请人照顾着,请人的艰难苦楚,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而小卢照顾我年已望九的父母近三年,尽心尽意,到2002年,因要照顾自己的母亲,才离开我家。后来,我父亲03年去世,她还特地从宁乡赶来吊丧,一进门,就抱着我瘫在床上的母亲,抱头痛哭,这份情意,是我永远也忘记不了的。她回乡后,我们也还陆续有些联系,近年来,她多次来电话,邀我们去做客,于是,我们才有了这次宁乡之行。
快到到宁乡的时候,她的儿子,就从他打工的地方上车接着了我们,又坐了2个钟头的车,就到了沩山脚下的茅屋湾。一壁青山,一湾曲水,青山碧水之间,一条公路扭头一甩,就钻进沩山去了,河湾里,新房,两层,白瓷砖外墙,就是小卢的家。她、她丈夫、挺着大肚子的儿媳,都站在禾堂坪里等着我们,一番亲热、一番问候,手忙脚乱的接待,丰盛的午餐……就好像久别的亲人回到了故乡。
冬阳下的村民
看了密印寺回来,还只4点来钟,冬阳暖暖的,溪沟旁、稻田里,一片忙碌,那是村民们正在做红薯粉,这种场景,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这条溪沟,他们叫大河,实际就十来米宽,很久没下雨了,所以水也不是很多。
洗干净,用机子粉碎后,就集中到这里来加工了。
粉碎后的红薯,用布袋装好,放在一个特制的木桶里揉挤,粉子随水流出,到下边的水泥池里沉淀,渣子则留在布袋里,可以喂猪。
沉淀池中的水被放走后,捞出留下的红薯粉,放在晒垫上晒干,就是干红薯粉了。以后再加工,可以出多种产品。我们是将其煎饼吃,甜甜的,极有劲道,好吃极了。
火塘边的夜
苍茫的暮色,从天边流淌下来,一会儿,天就黑透了,袭人的凉气也伴随而至,于是,厨房的火塘里,旺旺的柴火燃了起来。大家挤坐在火塘边,说着闲话,听到正房里传来了新闻联播的声音,有几个就起身烤煤火看电视去了,于是,火塘边只留下了小卢、她的媳妇、和我们。我们围坐着,暖暖地,闲闲地,静静地,一边看着火舌跳着怪异的舞蹈,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回忆着在我家的往事,讲述着她家翻身的艰辛,有时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柴梗从火中爆裂,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
夜,静静的,远处溪沟里平缓流水流过石滩的声音,似乎都能听见。
清晨的村庄
一大早起来,我们便踩着淡淡的晨雾,到村子里去乱逛去了。没想到,这还是一个蛮大的村子,石板小路,通向一户户人家,有的开了门,有的连门都没打开。房子有破旧不堪的,也有新建的,但新建的似乎还是较多。农村里,一家的客人就是一村的客人,遇着的人,都和我们打着招呼,笑着,把我们往屋里让,甚至邀请我们和他们一起吃早饭。在一户人家的门上,我看见了一幅很有意思的门联,“人近百年犹赤子 家存二老看玄孙”,我把它记下来了。
下面这个门楼的门楣上,还写着“第 生产队食堂”,看来是有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