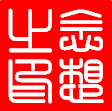我们农场的秋罗姐她走了
本月初的一个清晨,我接到一个不详的电话,我们农场长沙知青秋罗姐姐得糖尿病并发症已去世。电话是他爱人晏哥打来的,当天晚上我与农场知青朋友一块赶到水泵厂晏哥家里,安慰晏哥节哀顺变。在追悼会上,我们为失去当初一起战天斗地的知青朋友而感到悲痛,我们追忆农场知青生活的酸甜苦辣。人生苦短,怎么秋罗姐就走了咧?
晏哥是65年下放到怀化县良种示范繁殖场的长沙知青,。我70年4月下放到农场时他那时在坐牢,听说是收听敌台广播而被人陷害的。到我们当年下放的下半年晏哥回到了农场,那时我们在大田干农活都一个个晒得黑黑的,晏哥一脸苍白的出现在我们面前,反差很大。我们不敢和他打招呼,离他远远的。农场有一个从长沙一中来的回乡知青,66届高中毕业生,是邵阳农村考入长沙一中的,听说当时是长沙一中红卫兵团的团长,也不知这位回乡知青通过什么办法又变成了城市知识青年,并和70年3月第一批(当年)长沙知青下放到了农场。农场有很多从县城和地区下放的右派分子,还有像晏哥一样收听敌台的而坐牢的长沙知青和本地知青。回乡知青狠抓阶级斗争来不来就在宿舍里举行批斗会,一下批这个、一下批那个,反正这样的事情我从来不参加。我记得有一位长辈给我说过的三句话,不要瞧不起乡里人、不要在人家倒霉的时候踩人家、更不要在人家得意的时候捧别人,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也许正因为这样,那位回乡知青也不太和我打交道,我更不屑于和他交往。他是农场团支书,今天找这个知青谈话,明天找那个知青谈心,尤其是女知青他更是热心。对于晏哥和秋罗姐谈恋爱,他更是不看好,秋罗姐也是不怕他,经常被秋罗姐呸得焦干的,秋罗姐也不顾一切的与晏哥结了婚。那时农场大部分长沙知青还是齐心的,男知青看经常批斗这些有问题的人,干脆一个个剃成光老壳,也不去搅这潭浑水。(去年我和同学到怀化,我只去和原来农场长沙知青见了面,尽管这位回乡知青在市政府机关混了个一官半职,我也没有想见他的兴趣。)结果像我们这些知青就入团比人家晚,招生读书也由于家里七里八里的问题政审过不得关一拖再拖。
农场有好多子弟在附近的学校读书,农场要派一位老师去教书学校才肯接纳农场子弟读书。那时我和其他3位长沙女知青在农场被职工号称为铁姑娘,农场领导还是对我蛮好的,场长说:“我们通过研究,还是派你去教书,你文化水平高一些,(那时我经常在县城借到一些外国名著,我姐姐要好的同学在怀化县中医院工作,她那儿经常有借来的书。)那时我在农场几乎就是靠这些书籍蔚籍着我的灵魂,靠这些书打发着这漫长而难忘的岁月。劳动收工回宿舍我总是捧着一本本大部头的书在看,农场领导误认为我比其他知青朋友的文化水平要高,就要我去教书。当时我怕去教书就不会有招生读书的机会,死活不肯去。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上大学读书或去图书馆工作。农场领导说:“我答应你,下次第一个去读书的人肯定推荐你,你还是安心去教书吧!”我还是说:“谢谢农场领导对我的关心,我还是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没有办法园艺排(我们那时都是以排为单位,农场是一个连,县级才是团级架子)的一个工人替换了我,我就又从大田到了园艺排。几天以后,秋罗姐找到我说:“我和你换一下排怎么样?”我说:“怎么了?”“你看落,我的脚这个样子,去大田做活很吃力,我和你换一下不下水的工作我的脚就不会那么痛”秋罗姐如是说。也只怪我们平时关心秋罗姐不够,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脚和别人确实不一样是牛蹄花脚,一双脚背上亘起了坨,其实这是很明显的残疾,这样的长沙知青是完全可以不下放的。只怪秋罗姐她们街道上的差东西无情地将她下放到千里迢迢的怀化农场,真是太无天理了。秋罗姐家是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我记得她们家住在经武路铁道边,矮小的偏唰居住了一大家子,火车的轰鸣声离家是这样的近,那时我还诧异她们怎么能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也许是弱势群体,她也只能这样接受命运对她的安排。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和她换工作的要求,我们不关心她谁来关心她?秋罗姐的脚是这个样子,可以想象在农场的日子里,她不仅要承担下放期间她所要承担的精神压力,更要承担身体残疾所带来的痛苦。直到晏哥和秋罗姐回长沙之前她一直就在园艺排工作。后来我去读书、教书放寒暑假一有时间路过怀化总忘不了去农场看望晏哥和秋罗姐以及她(他)们的一双儿女,他(她)们也会倾其所有来招待我们这些知青。
去年下半年,我们农场知青相聚在市交警队工作的长沙知青同学家里,大家都在回忆农场知青生活的点点滴滴,晏哥和秋罗姐也和我们欢聚在一起!谁知这么短的时间秋罗姐就这么永远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饱受疾病折磨的秋罗姐就这样走了,也许走了对她也是一种解脱,在天堂她一定会感到很快乐!因为她一直是个很快乐开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