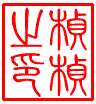三自一包的威力
在湖区干过的知青,一定都忘不了每年春天,那一望无际的红花草籽田。
是的,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红花草籽是早稻的当家肥料,其被农民重视的程度可想而知。
在我插队的地方,田多劳少。需交派购粮的田人均四亩多,还有许多见天收的湖荒甩亩。
这么大面积的田地,又基本都是双季稻,因此,每年必须留下不少红花草籽做种子,这就叫做种红花。
种红花老透后,需及时收获,晒干脱粒。这就需要老天赏脸,晴上几日才行了。
可是69年夏初,在该收获种红花时,老天就是不开脸,阴雨连绵,下个不停。队里几个干部急得跳,种红花若是沤在了田里,明年的生产还怎么搞?
就在大家将要绝望时,雨突然住了,有经验的老人都说,天老爷开眼咧,这下要放晴了。
傍晚收工后,生产队长兴发哥,站在村子的中心点,我们房东奶奶家的禾场上,扯起喉咙大声喊:恩朝晚上开会啊!各家各户不准缺席啊!
这生产队开会,我们早已领教过,拖拖拉拉,疲疲塌塌,人到得三不六齐。干部们先讲世界形势一片大好,再讲国内形势非常喜人,直讲得大家昏昏欲睡,东倒西歪。今天晚上的会,一定又是老一套。
吃过晚饭,我们慢腾腾地走进会场,却发现会场已座无虚席,各家各户不象以前那样只派些妇女、小孩来敷衍应付,那些当家的大男人都亲自来了。
大家满脸兴奋、交头接耳,会场里一片嗡嗡的说话声,充溢着一种不同以往的热烈气氛。这是怎么啦?有什么喜事吗?
兴发哥从那盏昏暗的煤油灯旁站起来,吭吭清了两下嗓子,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兴发哥性格急噪,讲话十分有特色,本地粗话可以非常贴切地夹带在他的方言里流畅地讲出来,却并不显得粗痞。
我们听惯了,不以为然。然而有次一位同学来玩,晚上正逢生产队开会,听到了他的发言。同学在笑得直喊肚子痛的同时,不忘做了个初步统计,结果是,队长的讲话平均每段有粗痞词5个。
兴发哥清完嗓子,开始讲话了,他一反以前的罗嗦套话,开口就切入正题:恩娘的bi哒的,这个杂种的天老爷,总算开啊脸哒,俺要抓住好天时,把种红花抢收回来!不然就夹lan哒!哪么抢?我个人有个想法,这次俺管他奶奶的搞一盘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要快点搞,争取明朝一天搞完,不然高头一晓得哒那个jiba日的就搞不成哒!
特色发言一气呵成!会场静悄悄的,二三十双眼睛盯着那盏小小的煤油灯,煤油灯后面坐着老会计。
老会计站起来,他简要地讲了这次行动的原则,即所有种红花田按劳力分到户,工分按亩计算,为了调动大家积极性,每亩单价定得非常高。
人们脸上的表情随着老会计的讲话进一步兴奋,老会计问大家还有么得意见啵?众口一词吼出两个字:没得!
接着,老会计拿出一张纸,宣读起来:新鸡婆家,搞过水丘,观老爷家,搞大担丘,黄毛家,搞……我们认真听来听去,最后才听到:青年家没得男劳力,就搞全婆屋前头堰塘边那块小些的算哒!
说老实话,这种红花到底应该怎么收割,我们并不知道。听见只分了一块小的给我们,心里多少有点不服气。但坐在我们旁边的花鸡婆告诉我们,收种红花是狠工夫,您几个女儿会奈不何的。我们也就算了,小的就小的吧。
散会后,我们四个人商量明天怎么干,最后决定早点起来,早点干完,收个早工,到隔壁队的同学哪儿去玩。打好小算盘后,收拾睡觉。
这一觉睡得太舒服了,迷迷糊糊中听见房东奶奶那急切的喊声:大G、小G、小L、小Y,您几个还没出去啊?别个都快搞完哒!
我们惊醒过来,穿好衣服打开大门一看,哇!太阳已挂在了半天空,这下糟了,怎么睡到了这个时候啊?
嗨!这怪谁呢?平时出早工,队长打雷样一声喊:架势哒……我们睡得再沉也会惊醒来。怪就怪今天搞三自一包,不用喊工,也没人喊了,所以我们睡了个天昏地暗,把起早床,收早工的计划丢到爪洼国去了!
急急忙忙扒了两口剩饭,抓起镰刀跑出村子,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目瞪口呆:大田里一家家男女老少齐出动,割的割,挑的挑,男劳力清一色赤膊上阵,女劳力裤脚袖口扎起老高,老人、小孩也没闲着,一片你追我赶,劳动热情冲云霄的动人画面。
我们下乡以来,可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壮观的劳动场面,这和平常出大寨工,干部在前面吆喝,社员在后面磨磨的场景形成鲜明的对比,看来,这三自一包,威力还不小啊!
来到我们的那一小丘田边,只见种红花经雨水沤了几天,已经全部倒伏,枝枝蔓蔓纠缠在一起,我们一时竟不知如何下手。
又到旁边田里看别人怎么干,看了一阵,才明白要一边用镰刀把根割断,一边顺着倒伏的方向向前滚动,把它卷起来。
于是,我们四个比葫芦画瓢干起来。干起来才知道了我们那句长沙俗语的涵义:“包子各样大,饺子各样长,看事容易做事难!”
那又湿又重的种红花根本就不听我们的指挥,两只手顾了割就顾不了卷,顾了卷就顾不了割,只干了一小会,我们就腰酸背痛、腿脚发麻、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个个坐在田埂上喘粗气。看别人家的工作都已进入尾声,不由焦急起来,这怎么办啊!
这时,老会计挑着一担种红花经过,看见我们,放下担子:您几个还只搞了这点点啊,也难怪,这哪是你们青年奈得何的工夫。
小伙子立中也挑着担子过来了。立中是个回乡知青,平常对我们也蛮关照的。见我们狼狈不堪的样子,犹豫片刻说:“几个青年搞吃亏了吧?要不这样,您几个把这丘田让给俺屋里算了,俺屋里那一大块已经搞完哒咧。”
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四人立即将眼光投向老会计,眼巴巴的望着他。
老会计是我们刚下来时的房东,他和他母亲奶奶一样,对我们几个女知青的关心照顾胜过了自己的亲人。
老会计连连点头:要得、要得!立中你做点好事,这工夫要这几个女儿做,造孽咧!队长那里俺去讲。
就这样,我们舍弃了那搞三自一包分来的种红花田,舍弃了社员们认为是天上掉馅饼的高工分,象我们原计划的一样收了个早工,高高兴兴地出去玩去了!
一路走,一路傻乎乎的讨论,队里要天天搞三自一包就好了,那样的话工夫有人抢着做,我们肯定用不着这样累死累活的天天出工了。
当时十六、七岁的我们,虽然涉事未深,但农民对三自一包那种发自肺腑的拥戴,我们却留下了深深地记忆!
令我们想不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这偷偷摸摸搞的一次三自一包,已经象萌芽,象星星之火,一遇改革开放之东风,便迅猛燃烧,以其巨大的威力和能量,迎来了祖国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