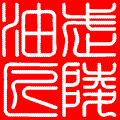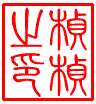恶 疾 缠 身
人生分寿、夭二大类人群,或寿、或夭。
我认为自该属长寿一类,原由有。其一,心静,脑壳不太蛮想事,心宽体胖,不为流言蜚语所累。其二,食杂,凡对健康有益,甜酸苦辣均能吞食。其三,好动,有益于身体活动都积极加入。其四,遗传,父母年寿均近八十(父因小疾,误诊而逝,是年七十有九。)。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自幼口腔上腭有一凸块,数十年不痛不痒,不碍饮食,也就与之和平共处了。谁知它也有不安分之日,却在我尽力保持健康身体赴奔花甲年之季,迫不及侍地跳出来作乱。
早两年,这凸块稍有变色,被牙医窥见,劝早除之,我不允,随它去。次年,去体检,口腔医生建议立即割除,防后患。言:仅四百元手术费。其实,我已动心思,此言一出,心中不快。
早些日子,单位客车被摩托擦刮,被摩托车主敲竹杠,非去大医院验伤。区区擦伤,个人所为,本可不理采,抹点红药水即可。现应宽仁以人为本,去医院检查,无妨。挂急诊,入诊室,穿白大褂者,虽慈眉善目,可开处方却不含糊,如宰人的饭铺老板,企图让食客掏空了口装,还想剥掉食客身上衣裳。先开了数百无的跌打损伤的丸、颗粒、水剂。又拍片、CT、B超、抽血等化验检查单据一沓,花费千余元之巨,为之气愤。那穿白大褂者意犹未尽,仿佛还要来点什么名堂。心想:还会不会还作开腔探查吧?累了一晚,无事而终。(经交通执法部门裁定,对方负全责。)
此后,对医患关系心存疑虑,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医生之语均散发着铜臭味,因不识好歹。其实,医生手术先不言钱,完后,结帐,收取四百元,我会照付。哎,迟了,后悔无用!
第二年春,上腭凸块溃疡,去诊所,服药,打吊针,久治不愈,我仍若无其事。医生告之,本“庙”太小,速去大医院。我去大医院,挂教授号,看病。教授一瞥,病情不简单,留人,住院,通知家人。
住院,开了一大沓各类化验单,将排泻物和抽出的鲜血送进化验室。X光拍片、CT、B超、心电图,挨个尝试。痛苦的要数上腭切片检查,未上麻醉药,医生用刀在患处切下一块。顿时鲜血直涌,他用蛋大的棉团(捏紧),塞进口腔,鲜血和唾液立即浸透,数小时后血才止住。病友惊诧,我笑而对之。
折腾三日,我确诊(快片)为上腭CA。医生对家人说:乐观估计术后,重则失语,轻则需一年半载不能发音,均难预料。我看家人凄凉色,听亲朋慰藉语,坦然,人畏死,何必作茧自缚。我静念解脱之法,心安气则顺,五脏六腑亦和,食则味甘,药方才有奇效,病自怯。然则“人大言,我小语;人多烦,我少听;人悸怖,我不恕。”随遇而安,岂不乐哉。
我被推进手术室,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将上腭切除了一半,医生怕CA细胞窜入鼻腔,来了个撸草打兔子,顺带将左鼻腔切掉。开始几日尚未拆线,头部肿,双眼迷成一线,看不清东西,全凭耳朵听。嘴巴内密布缝合线,只能靠点滴,吸食流汁,补充能量。我不能语,急,想说,用笔,几日用纸一大沓,有时干脆点头、摇头作答,想:哑语,有用武之地了。几天后,肿渐消褪,拆线,舌头灵便了。我依依吖吖,言语含糊,竞能说得完整的句子。医生高兴,称手术非常成功,比想像的要强多了。
再次切片检查,鼻腔和其他部位未检出CA,放心!我听后,难过,干吗切这么多,鼻腔又没碍事,给切了。真是城门失火,泱及池鱼。仔细再想,医生也是负责任,应当谢谢。
术后,我躺在病床上,亲朋好友汾至沓来。对来探视者一一至谢。后心理复杂起来,倍感失落与凄凉。
上腭原件被切除,口腔内挖了个空,面部凹下去一块。左面部如两条大蜈蚣趴着,破坏了平衡,不再成轴对称了。上年纪爱美之人,去做拉皮整容手术,术后容光焕发。我却反其道而行之,绷着个脸,象别人借了我的米,还了糠似的,笑起来难看,自觉恐怖,自言自语地说:就这样去见阎王爷了,他老人家可能见到我这付容貌,在阳间受过苦,可能顿起怜悯之心,被留在他身边搞个文职人员,免受下油锅或地狱之苦,有可能偷偷给网友们添加阳寿,也积德了。
出院回去休息几日(还要回医院做放射治疗。)时,还霸蛮,非要从附二院步行至东圹,乘601路车归。怕在街上行走,公开了自己的色像,引起市民围观,影响市客,特意带了付墨镜,还将草帽压得低低的,别被认为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离院出走,抵达长沙。因行动迟缓,仍避之不及,被美女发现,住足观望,不好扫他人的兴致,只得免费任其目睹狰狞面目。心想:美女,你别用爱斯美腊达的那种眼神看着,我不需要怜悯,别看我像貌丑陋不堪,可不是巴黎圣母院的那位双耳被钟震聋了的卡西莫多。几天前,本人模样还对得住观众,现在可真对不住了,千万别被吓着,我可是位怜香惜玉的绅士。真有春光易逝,伤疤难偿之痛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