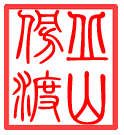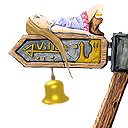邱 某
大名叫邱益康,邱某是他自己叫出来的小名。每当他要发表什么意见时,总是以“我邱某人认为…”作开头,久而久之,大家就叫他‘邱某’了。其实大名原本也不叫邱益康,而叫邱一匡,就是匡扶天下的意思,足见其令尊对他的厚望。邱某的父母去世较早,由他曾在国民党时期担任过高官,后又担任政协委员的伯父抚养成人。在那个动辙得舛的年月,他伯父觉得‘一匡’二字太过张扬,遂改名为‘益康’。认为有益社会,身心健康足矣。
邱某不是同校同学,却是一起去农场的,大约六七年中调到向阳队来的。好读书,善言谈,性格耿直,喜争胜负。身板挺直,相貌俊朗,却不喜欢搭理女同学。常穿一袭旧的直领学生装,必定把领口风勾扣得紧紧的。动作敏捷,走路迅疾,颇有行武风度。他祖籍浏阳平江交界处的官塘,是个出将军的地方。据说邱创成、邱会作都是他的本家。我想,一定有较深的家风影响。
他最欣赏两句话。一是:“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是孟子说的,当时我们都知道。二是:“向使天下无孤,则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是曹孟德说的。后来他推荐我们读到《让县自明本志令》时,才知道的。每当他朗诵这句话时,总是挺着胸,昂着头,摇摆着身躯,体味着那种荡气回肠的韵致,仿佛他正身处诸候纷争的汉末,他就是秣马厉兵,雄踞中原的魏武帝。《让县令》中,曹操还写道“春夏攻书,秋冬围猎”。邱某特别佩服曹操,向往这种生活状态,认为是磨励自己文韬武略的最好方式。他把在农场累得两眼发黑的生活看成是这种方式的翻版,所以乐观豁达,等待施展抱负的时机。
六八年,中央文革的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说:“凡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必须有工人阶级进驻。在农村,则由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进驻。”于是,我们这些下放农场并单独组队的中学生又成了知识份子,面临再次下放。我和吴晋,陈启琳等十来个男女同学被分到石头水。邱某被分到田美生产队(上篇往事中提到的一个古老的村庄。)朱逖和他撘伙。曾和我说过一件趣事。邱某口味重,菜吃得很咸,朱逖受不了,常因此而生争执。一次,邱某煮了一碗酸菜汤,先是淡淡的,上桌后,邱某用筷子在汤中划一线,说:“你吃得淡,吃那边,我吃得咸,吃这边。”然后抓把盐放在靠自己这边的汤里,还一个劲地说好吃,朱逖哭笑不得。
也是那一年冬天,农场工区组合一批人上山倒树锯板子,没有家小的知青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和石头水队的几个同学,曾树林,吴晋被抽调到田美,吃、住就在邱某那里。田美的后山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原始林木。郁郁葱葱,遮天蔽日,野猪,黄麂,穿山甲,野兔经常出没。蛇,蜥蜴,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爬行动物常在脚边淄走。甚至还有山豹带着崽子路过,据村里的老猎手说是翻过这山头去与四十里外的蒋家大岭上的公豹会面。虽是冬天,也只是多了一丛一丛的红叶,黄叶,把山头奌染得斑驳绚烂,更富色彩和活力。太阳出来前,山雾濛濛,到处是湿漉漉的,早上出工上山,还没到工棚处,从头到脚都滴水。最难为的是邱某了。凭添了几条大汉吃饭,我们虽带了一些米和油,但定量少得可怜,不足以吃饱,而且倒树锯板子是重体力活,饭量还特大。邱某不得不想着法子掏红薯,挖芋头来填饱大家的肚子。最让他为难的是菜,他有块巴掌大的自留地,平时他一个人还凑合,冬天里已是残枝败叶,拿什么去做成下饭的菜?他只得东借西讨,讨不到就出奌钱买,为的是让我们吃好。侭管如此,他每天乐呵呵的,一边锯板子,一边还哼着谁也听不懂的小调,收工下山,我们累得不想动,他却要端着个畚箕准备饭食。饭后,照例是谈古论今的时候,大家围着火圹,烧着枫树兜芭,上下五千年,天文地理,诗歌对联,逸闻掌故,一顿乱扯,他当然是主讲。现在还记得的是他讲曾国藩挽乳母联和平江举人在北京如何暗对翰林所出联题。后来,他不知从哪儿弄到一付谷牌,奌着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玩开了。他打牌很认真,出错牌输了就不停地摇头,口里喃喃念叼:“出错哒,出错哒。”主动受罚,就是用夹子夹耳朶,或是在脸上贴纸条。一但羸了,高兴得顽童似地大笑,主动地替别人夹耳朶贴条子。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月,任务完成了。分手的那天吃过晚饭,他再三恳留我们住一晚,我们几个的女友都在石头水,也祘是归心似箭吧,还是与他告别上路,他送我们到两里路外的马鹿头路口,低声说了一句:“唉,一晚都留不住。”朝我们挥挥手,转身走了。我犹豫地站着,望了望暮霭中他摇摆的背影,还是转身赶上远去的同伴。
七三年,我在长沙做上门木匠,就是到别人家里做家俱,以此来养活自己和替淮海治疗眼病。一天,正背着锯子,刨子匆匆赶往主家,在南门口与邱某不期而遇。他那时住在南门口附近的沙河街伯父家里。几年不见,竞无语相对。我那时由于生活窘迫,而衣衫烂褛,面容憔悴。他上下打量我一番,说:“等我一下,”转身走进南门口百货大楼(当时叫联成),一会出来,手里拿着四包枫叶牌香烟,急急塞到我兜里。说了声:“兄弟,多保重,后会有期。”转身走了。我那时抽烟最贵不过是两角钱一包的‘岳麓山’,而‘枫叶’时价三角四分。
记得有一年我过生日,淮海买了一包三角二的‘卢山’,我连呼:“奢侈,奢侈!”现在看来,当然像笑话,却怎么也笑不起来。
此后,再也没有见到邱某了。每逢知青同学聚会总是想起他。听说,他遵伯父之命,回到了平江老家,娶妻生子,接续香火。后来我找人四处打听他的消息,甚至和平江水电局一位叫邱救兵的副局长通过电话,因为有人说邱某曾在水电局工作,并改名为邱救兵。我虽不信他会改名,还是联系了,果为谬传。他生活得怎样?在干些什么?时有想念。直到05年秋,朱逖打来电话说,找到邱某了,还在平江老家,给了电话号码。我兴奋不已,当即打电话给他,传来果然是邱某那仍然昂扬的声音,我们约好了到平江见他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