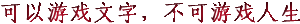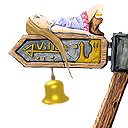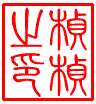平凡并不一定简单,伟大并不一定神秘。 ——雨果
(一)
我第一次见到闵立宏,我就觉得她应该去当一名女兵。那一瞬间的感觉,在我心中已经保留了四十多年。
闵立宏高我一届,是长沙市四中(现在的周南)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当时的模样:瘦高的个子,走路劲蹦蹦的。一头短发,扎着一个大刷把。那是六十年代女学生时髦的发式,只是她扎得与众不同的大,老远就看见那把头发一翘一翘的,显得特别神气。
那时只听说她的父母亲在台湾。她两岁时由父母带上了南下的火车,是送行的舅舅担忧她小小年纪经不起颠簸之苦,在汽笛鸣响的刹那间,将她从车厢里抱了出来。从此,她在奶奶和亲戚们的拉扯下长大。从此,她戴上了一顶沉重的“台属”帽。六六年,又听说她的档案中写着 “不予录取”四个字。在那个“血统论”盛行的年代“台属”简直是“十恶不赦”的代名词。然而闵立宏表现出的开朗大方让她成了学校有名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出生职员家庭,祖辈是地主,属于团结对象。也许是因为这种身份的圈定,在我十七八岁的年龄,就对她有了深刻的印象。我每次看到她头上的大刷把翘翘摆摆时,心里就有种隐隐的痛,有一种莫名的想要接近她了解她的欲望。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们同一批下放到沅江县黄茅洲区子母城公社。知道她分在相邻的东红大队,却一直未曾见面。一年后我被招工回到了长沙,就一直忙于自己的工作。几年后,听说她和当地的一个农民结了婚,而且是一个比她大十八岁,丧妻、拖着三个儿子且家徒四壁的农民,我感到非常震惊。后又得知那个农民的前妻,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妇,因不堪贫穷和病痛的折磨竟丢下几个幼小的孩子(其中一个还在吃奶)自杀了。而闵立宏,一个在城市中长大正值青春的女学生竟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他的生活,承担几个幼小孩子的母亲,支撑起一个贫困破碎的家。
我百思不得其解,心里一直为她叫屈。
她过得好吗?这个问题萦饶在我心里将近三十年。直到一九九六年,通过一些迂曲的关系,我终于得知,她还在沅江,还和那位老农民在一起。当了二十多年的乡村教师,台湾的母亲也与她联系上了。我终于忍不住给她写了封信,表达了我近三十年来对她的牵挂与敬重,并希望与她交朋友。她很快回了信,很感动我这个素不相识的校友这样看重她。我们开始有了书信联系。一九九八年寒假她回长沙探亲,特地来我家与我相聚。从此,我的亲友中有了一位立宏姐。
(二)
她来我家的那天,一接到她的电话我就激动不安地等待着她的到来。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老人,我已经认不出她来了。这是闵立宏吗?她看上去很憔悴,远远不止五十一岁,头戴一顶老年人常戴的深红色毛线帽,穿着一件暗色棉衣,记忆中那个开朗大方的女孩的印象消失殆尽。只有她的眼神中透出的几丝刚毅还为我所熟悉。
她微笑着说:“认不出来了吧?”
为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牵肠挂肚三十年,我以为与她见面会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她带来的却是一团和风细雨,让我的心情很快地平复下来。
陪同她来的还有一位少妇、一位小女孩。 “这是我媳妇,这是我孙女,叫思思。”她出口就是沅江方言,语调平缓,淡淡的。
开始都有点拘谨,不知说什么好。因为这样面对面的说话,在我们还是第一次。后来,各自谈了些家中近况。她告诉我,她有四个儿子,都在家务农。最小的儿子铁军是她亲生的。她仍在子母城学校当老师,丈夫跟她住在学校。逢年过节儿子们就轮流接他们去团聚,一大家人相处很融洽。
吃了中饭她们就走了,像来去匆匆的一阵风。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深深的惆怅,像被打翻了五味罐,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我想,许是每个人对苦难的理解不同吧,你认为无法忍受的屈辱和困苦,她却把它细细地揉碎了,自然而然地掺进了她的生活,成为了她生命的一部分。
我渴望着能够真真切切地了解她。
2000年8月我带着上大学的女儿到了我当年插队落户的沅江县黄茅洲区子母城乡。
离别子母城整整三十一年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条条绿荫掩映的宽敞笔直的道路。记忆中的泥巴堤道没有了,芦苇杆和稻草盖的茅草屋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砖瓦房组成的城镇般的村民住宅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农田整齐规范,井然有序。
立宏姐指着一条宽阔的水渠说,这里就是咸康大队的原址。我曾经插队的地方,我曾经的知青生活的记忆已经成了一条宽阔的水渠!听流水哗啦啦地响,我的眼眶湿润了,我的黄茅洲,我的子母城,我根本认不出你了!
我此行的最大目的就是想看看立宏姐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很想深入地与她聊一聊。
她所在的沅江县黄茅洲区子母城学校是一所初级中学。仅有一栋两层楼的教舍和一个大操场。因放暑假,教舍的墙和桌椅都蒙上了湖区特有的一层细腻的灰白色泥土,室内设施桌椅板凳都非常简陋,却有了四十多年历史。教师宿舍有新旧两栋,就在教学楼的后面。
立宏姐的家就在旧舍的一楼。那是一进两间房,水泥地,墙壁的白粉脱落得斑斑驳驳。前面房间有书桌、教师用的书柜、两张藤靠椅、一张简式木制双人床;后房也有张简单的双人床,一个旧衣柜,两个木箱笼。穿过房间是约十五个平米的露天洗漱地,接着是厨房,出了门便是一块菜地。没有一样多余的东西,没有一件漂亮的摆设。
家虽简朴但却让一路暑热灼烤的我倍感舒爽。我对立宏姐的现状约感安慰。
我终于见到了立宏姐的丈夫—-陈学纯,一个七十二岁老人,他显然很开朗。令我惊讶的是,湖区农民那种常有的粗黑,风吹雨打的黑皱纹在他身上没有,倒像城里老人似的白白净净。他穿着白短袖园领汗衫,黑色薄棉绸裤,个子不高,一双小眼睛总在笑。
立宏姐低声地告诉我,陈爹的身体不好,近几年常令她提心吊胆。现在她最怕的是在课堂上有人跑来喊她:“陈爹又晕倒了!”
趁立宏姐到医院去看待产的三儿媳妇,我就和陈爹聊了起来。他坐在藤椅上,笑眯眯地告诉我:“我和闵立宏不是我追她,是她追的我。当时别人要给闵立宏介绍对象,她怕不认识的人难得了解,来征求我的意见。并说她相信我,情愿和我结婚。我这个人不催老,性格脾气也好,她都了解。”
他知道我的来意,显得很自信。 言谈中,他谈到因为和闵立宏结婚,他差点丢掉了党籍的事。“公社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要党票还是要老婆。我说党票也要,老婆也要。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为什么不能和她结婚?”
因为三儿媳难产,立宏姐每天在学校与医院两地奔波。为了不影响她,我和女儿只好匆匆告别,连照片也没来得及与她拍一张,来之前渴望能与她作深入地推心置腹的长谈,又未能实现。
陈爹简单的几句话让我隐隐地感到,他们之间的结合绝不能按照世俗的标准去衡量,两个孤苦的人相互依存的爱已经让一切忽略不记。
(三)
再次见到她是在五年后了,我又一次由女儿陪同到了沅江,立宏姐的体态有些发福,脸色红润,精神显得好多了,只是背稍有点弯。一进她的家,就感觉亮堂了许多:地面铺上了白色的瓷砖,墙壁刷白了,原放藤椅的地方摆上了一张简式长木沙发。有了一台老式的电视机,电话也装上了。
陈爹不在了!他于2003年因脑溢血去世了。睹物思人,看到这张木沙发我便想起了那张藤椅,想起陈爹端坐在上面让我拍照,笑眯眯地讲述他和闵立宏的故事。立宏姐说,家里没有陈爹太寂寞了,她一个人不想住。上初中的孙儿陈彬和上小学的孙女陈思思陪她住在这里。休息日儿子便把祖孙仨接回家。
每天清晨五点半立宏姐就起床了。她很快做好早饭,照顾两个孙儿吃过饭去上学。我也跟着过了几天早起早睡的日子。在她家的几天,不管是在外出的路上,或是她做家务的空隙,立宏姐便会断断续续给我讲述她和陈爹的故事。
1971年后,闵立宏那个小组的知青,招工的招工,回城的回城,最后只剩下了她一个人。每次招工贫下中农都推荐了她,却都因“台属”问题被刷名。
闵立宏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虔诚地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什么累活苦活都干,连男劳力翻凼子这种重活她也干。队里的双抢任务很重,因抢时间半晚就要起床出工。知青组有闹钟,社员希望他们能叫大家起床。闵立宏主动承担了此事,每天半晚她便跑遍全队挨家挨户地叫社员起床出工。
农民注重实事求是,他们看重闵立宏,把她送到大队小学当了民办教师。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这是知青诗人郭路生那首著名的《相信未来》。诗所表达的悲怆和忧伤的乐观旷达使闵立宏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她由衷地喜欢这首诗,好像这首诗是专为她写的。寂寞的时候,她常常独自呤诵着。
也许是种命定的缘分,知青屋最近的邻居就是陈学纯家,陈学纯平时就很关心知青,在闵立宏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他常让八岁的儿子贵安过来陪伴她。贵安精精瘦瘦,机灵乖巧,他和弟弟贵财特别亲闵立宏,闵立宏也十分同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