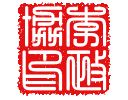知青岁月里的烟民

知青中抽烟的不是很普遍,但也大有人在,比如本人就是一个烟民,如果说在学校时还是一个见习烟民,那么,下乡后就是一个正式烟民了,在学校有父母老师管着,只能偷偷摸摸地抽,成为知青后可以堂而皇之地抽了。
下乡前,好朋友聚在一起,有烟同享,初次吸烟还很不适应,出现过头晕,呕吐的现象,后来就习以为常了。当时的“中华”烟一块多一包,是最顶级的烟,我们想尝尝,但又买不起,只能买一两支试下味。
记得下乡那天,单位上除了送我“红宝书”以外,还送了我一堆香烟,有“青松”,“咏梅”等好几种牌子的,总共有十几包,我从未拥有这么多香烟,心里美滋滋的,初下乡的那阵子,确实“阔”了一把。
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在干校还真有点像当兵的,我们的编制是中队,排,班,住房是集体宿舍,吃饭是公共食堂,每月还发几元零花钱,这几元钱买完生活必需品,已所剩无几,那有钱抽烟呢,为解决抽烟的问题,我从家里带来烟丝,自制烟卷,自给自足。那时,大家都穷,烟民们抽的烟悬殊不大,最低的八分一包的“经济”烟,最高也不过两毛一包的“火炬”烟,能抽上“火炬”烟的,是令人羡慕的,与我同宿舍的L同志,他长年抽“火炬”烟,在我看来,他简直是一个“富裕中农”。他肯定是家里有钱给他,不然他不会如此之“阔”。在我的记忆中,三年的知青时期里,家里没有给过我钱,有时从家里带点粮票来,跟别人换点钱维持生计。
当时不只是知青中的烟民买不起烟抽,下放的干部也是自己卷烟丝抽,李保煌同志是部队转业的干部,有时我们做事路过他家门,他就热情地喊我们进屋歇脚,并且拿出他自己生产的烟招待我们,李保煌同志子女较多,生活比较困难,十一,二岁的孩子要进山砍竹子卖钱挣学费,常常看到他三个孩子拖着满满一板车竹子,在泥泞的小路上跋涉。
几十年过去了,知青时代的烟民有的可能不抽烟了,有的仍然保持着过去的习惯,由于时代的发展,阶层的分化,老知青们的生活状况,已今非昔比,有的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抽着软“白沙”,有的却在用公款抽着“芙蓉王”,这也许是“命”,我不禁要奉劝知青中的达官贵人:无论到了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曾为知青这个神圣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