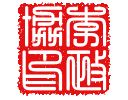四、任重道远
十六岁,是一个人成长历程的花季年华。按常理是在学校学文化,学知识的黄金时期。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却是有些不尽人意。那时城里的人初中毕业就得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叫下乡知识青年。乡下孩子一毕业就没有升学的机会,只有回乡务农一条路,叫回乡知识青年。
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回乡知青,开始我也感到十分茫然和无奈。那时的愿望十分单纯,就是想尽自己的能力为父母减轻一点负担,让含辛茹苦的二位老人晚年生活轻松一点,幸福一点。
有幸的是,在我离开学校回到家的第二天,就被大队聘为赤脚医生。所谓的赤脚医生,就是直接为农民乡亲看病的土医生。当时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但作为家乡父老乡亲的重托,我深感受义不容辞。同时我也坚信,一切事情只有用心去做,就一定能够做好。
随后我参加了公社组织的赤脚医生短期培训班。在针灸知识考试和实践操作考试中获得了第一名。初露锋芒,给了我干好这行的勇气和自信。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面认真学习专业书籍、一面虚心请教专业人士。那时公社卫生院有一位叫林锦红的中年女医生,她对我十分关爱。每次下乡巡诊都把我带在身边。看病、打针、上药,总是手把手教我。我也虚心好学,乐此不疲。半个月时间医疗点就筹备就绪,开张了。
公社医院的李院长夫妇也对我关爱有加。还专门派了一名叫梁中娥的卫校实习生来专门帮助我的工作。梁中娥是耒阳城里人,她年轻貌美,长我几岁。她处处把我当作小弟弟言传身教,耐心细致。使我受益非浅。据说她现在还在郴州医专任教。
为了拓展医疗点的业务。我还拜了一个叫刘芳支的草药郎中为师。从采药到加工,我潜心学习。一次刘师付带我去桂阳县的一个深山老林中采药,当时发现一根有口杯粗的勾藤长在一簇灌木丛中,并朝着一片见不到天的残枝败叶处往上攀延。为了采回这根罕见的勾藤,我怀揣柴刀爬到了这棵勾藤的上部。当勾藤快要砍断时,突然一条盘驻在残枝败叶中的足有碗口粗的大蛇,张着大口,朝我的头顶袭来。此时听到师付一声惊叫“头上有蛇”。在惊恐之余我连人带刀从一丈多
高的地方滚落到地上。来不及思考,翻身后我就没命地往山下逃去。一口气逃出了二、三里地,才停下脚步,瘫倒在一块大石头上。这是我的第一次历险。
在一个盛夏的中午,我一个人背着药箱,行走在一条上山的石板小路上。这条小路一边是长着一米来高的烤烟地、一边是正在抽穗的水稻田。突然烤烟地里一阵旋风刮来,一米多高的烤烟在哗哗地摇动。我睁大眼睛定神一看,一条黑乎乎的、足有水桶大的巨蟒,在离我不到一米的烤烟地里窜了出来,穿过石板小路朝长有水稻的田里奔去。在水稻中间穿行而过。我呆呆的站在石板小路中间不敢进、也不敢退,眼睁睁看着这条巨蟒在我的眼皮底下通过,足足有十分钟。这时我已被吓傻了。当这条巨蟒通了十分钟左右,我才缓过神来,拼命往山上狂奔。当跑到一片开阔地里,我实在是支持不住,就倒在一个土坡上。大概过了半小时我才继续上山。
下午四时我巡诊完后按原路返回。两位老乡一路护送我来到了巨蟒通过的地方察看。发现稻田的禾苗都向两边倒下,中间留下一条两尺多宽、一百多米长的水沟。这是我的又一次历险,回想起惊魂的一幕,迄今为止我还心有余悸。
在我任赤脚医生的日子里,我每天除了在医疗点坐诊外,大部分时间都是身背药箱,走村串户。足迹踏遍了全大队十个自然村。先后为上百父老乡亲送医送药。深得大家的欢迎和认同,理解和尊重。大家都称呼我为小刘医生。
在我的家乡有一个我十分敬重和同情的老人——他叫刘礼芳,按辈份我和他是同辈,所以我常称他为礼芳哥。
他满腹经论,少年得志。解放前是我们刘姓大家族的名人、才人和头人。他二十四岁就在蒋经国手下当了国民党青年军的上校团长。一九四九年初,他奉命带领一个整编团,增援已被解放军围困的北平守军,傅作义部队。后来傅作义将军接受了解放军的和平改编。他所率领的团也在改编之列。在北平期间他找到老乡黄克诚大将。黄克诚告诉他:“从旧军队过来的人,都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造,才能真正成为人民解放军。”并希望他去军政大学接受学习和改造。
他谢绝了黄克诚大将的善意挽留。因为他身上揣有一百八十块大洋。满以为回家后可买田置地安享太平。由于他不认时务,加上他厌恶了旧军队的黑暗政治,最后选择了回乡。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他怀揣大洋刚走出北平城就遭人抢劫,被洗劫一空。后来他再次返回北平找黄克诚。这时黄克诚由于军务繁忙,已去了天津。他没有办法,只好从北平沿途乞讨回到了家乡。
一九五一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作为旧官吏,被判刑入狱。文革中,又作为“黑五类”份子被揪斗。在一次斗争大会上,被造反派打折了一条腿。后来还被人用箩筐抬着游街示众。
在他六十岁生日那天,他怀着一腔悲愤和凄凉,在自己的土墙上写下了一副对联:
上联是:
六十载、贫不死、病不死、折磨不死,犹留残躯与诸君同度光阴,侥幸!侥幸!
下联是:
半百世、妻也无、子也无、衣食也无,鳏寡孤独与人世毫无相争,奈何!奈何!
横批是:
马齿徒增。(意思是:马的牙齿越多就说明越老,越没有用了。)
对于这样一位老人的坎坷人生,我十分同情。在他卧床不起的日子里,我力排众议,坚持给他进行针灸和草药调理。
误打误撞,几个月下来,在我的调理下,他居然能下床走路了。这是我在赤脚医生生涯中,做的一件善事、好事。这位老人在他的余生,一直对我心存感激。这也是我心灵上的莫大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