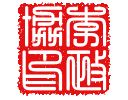一、家乡情结
从“纸都”耒阳市沿107国道驱车向南三十五公里,就到达了湘南重镇马田。国道旁耸立一块醒目的“黄克诚大将故居”的路碑,沿路碑指示的方向向西穿过将军街十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具有五百年历史的永兴县最大的集贸市场——油麻圩。
油麻圩位于永兴、桂阳、耒阳、常宁四县交界之地,是久负盛名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每月逢四、九开市,这一天四邻乡民人流如织,高峰时多达二万余人。几百年长盛不衷。
从油麻圩步行十分钟就到达了一个山清水秀的村落——东冲口。这里就是我的老家。
我的老家从明清年间时建村、迄今已有二百年的历史了。这里青石路面,青砖瓦房错落有致。新修的水泥公路直通村中。
村庄依山而建,座东朝西。村前面对着连绵数里的蛇形山,溪流潺潺的虎形山,还有绿树成荫的磨形山。村后背靠后龙山,山中长满了参天大树,有古松、香樟、红枫、梓木等。一望无边的万年松青翠如滴,四季如春。置身林中鸟语花香、松涛如歌、绿海如画。紧挨着村庄有两口清沏见底、纯净甘甜、四季流淌的清泉。一条小溪自南向北弯延而下。溪中有鱼、虾、螃蟹游弋其中,这里就是我孩童时代嬉戏、玩耍的天堂,也是我一辈子魂牵梦绕、难已忘怀、挥之不去的故乡故土。
在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我的祖辈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在这里繁衍生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我恩重如山的父母也长眠在这绿水青山之间。
据永兴县《县志》记载: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红军将领陈毅领导的一支部队由宜章出发,来到我的家乡与湘南暴动领导人黄克诚、尹子韵等人在油麻圩会合,发动武装暴动,据说当时有一千余父老乡亲参加。
我的祖父刘远奎从家中拿了一支猎枪随后参加了这支队伍,后被编入中国工农军第四军永兴红色警卫团。在井冈山不幸牺牲。身后留下我的曾祖母邓氏和祖母邓贵翠,带着我末成年的父亲、二叔和姑姑艰难度日,曾祖母于一九四五年病逝。我的祖母由于操劳过度,积郁成疾而双目失明,于一九六七年辞世。
二、感恩父母
我一生中最敬重、最崇拜、最感恩的是生我养我、疼我爱我、最勤劳、最善良、最伟大的母亲。她身材矮小、双眼混浊。头上总是包着一块青色头巾。她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良玉”姓欧。悦来乡马渡村人。她六岁丧母九岁丧父。少年时无依无靠,孤苦怜忊。九岁就到马田乡塘前村当童养媳。后来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幼年夭折,小的就是与我亲密无间,同母异父的哥哥——刘日德。
我的哥哥不到一岁时,他的生父因患病无钱医治英年早逝。一年后苦命的母亲拖着年幼的哥哥改嫁到油麻圩,婚后生有一女,后来丈夫被抓壮丁一去再没返回,小女儿也因病夭亡。
一九四零年,我苦命的母亲带着四岁的哥哥经人撮合与我三十多岁还未婚配的鳏棍父亲结合。这时我二叔也被抽壮丁去了江浙一带。姑姑也出嫁了。家中剩下曾祖母、奶奶、父母和哥哥五人相依为命,生活十分窘迫,为了维持一家生计,母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洗衣浆衫,操持家务,同时还喂养了一头母猪,每当母猪产崽时母亲更是通宵达旦、昼夜难眠。真是辛苦至极。
后来我的父亲跟人合伙,干起了杀猪卖肉的行当,由于家境贫寒,父亲从未进过学堂大门,终身一字不识。他身材高大、脾气暴燥、胆大心雄。伙计们都惧怕他三分。一路下来父亲的生意还算顺意,每一轮圩(五天)还能挣回一、二元钱的手续费,补贴家用。由于父母的辛勤劳作,一家人虽算不上富裕,但也算安定。
一九四三年我的大姐刘普彩、二哥随喊、二姐有彩相继出生,由于当时乡村的贫穷和疾病我的二哥、二姐相继夭折,只有大哥和大姐幸存,他们成了全家的寄托和希望。
我的哥哥刘日德两次随母下堂。一九六二年结婚。生有两男两女。一九六四年我哥因与邻村一个叫人宝的人发生争执,对方口不择言骂了我哥是野种。我哥不甘受辱,后来带着我嫂子回到他的出生地——马田塘前村。一九七八年因车祸身亡,年仅四十四岁。
我的哥哥一生坎坷,终身受苦,没有建树、没有成就。他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为人善良、忠厚一世。在乡亲中间留下了很好的口啤。
有人说好人自有好报,我的哥哥在他四十四年的苦短人生中,他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好人、大善人、大孝子。可能老天也有疏忽不公的时候,才让我哥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楚。有幸的是现在我的四个侄儿侄女都已长大成人。结婚生子。这也是我哥在天之灵莫大的慰藉。
我的姐姐一九四三年生,取名普彩。她小时候长的又白又胖,人见人爱。乡亲们都戏称她“三砣”“地主婆”。后来她读完初中.在当时一个贫苦的乡村女孩能读到初中毕业,真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可见当时我的父母对我姐姐的一片钟爱,期望值是很高的。
由于姐姐长相出众,穿戴入时。曾受到过很多人的亲睐。那时我的姐姐常常把我带在身边。我这个当弟弟的也沾光不少,出门时很多英俊青年经常暗地里要我叫他们“姐夫”。有时还少不了小恩小惠。在我们的少年时代、姐姐对我总是百般呵护,疼爱有加。也给我留下很多温馨的印记。
一九六三年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年,三年自然灾害。我的一家也逃脱不了饥寒交迫的厄运。
这一年,我的姐姐与当时还在广西桂林当兵的姐夫结婚了。在广西桂林我姐姐度过了她一生最美好、最甜蜜的时光。同年由于姐姐长得漂亮、使人怜爱,姐夫放弃了在广西桂林奇峰镇工作的机会。同我姐姐回到了老家。生有三男三女。
我的姐姐从小就受到家人的百般宠爱,生性倔犟。婚后由于六个孩子先后问世,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生活十分艰辛。由于家庭的重负、儿女的拖累,姐夫也积劳成疾,可怜的姐姐苦挣苦度,身心极度疲惫,面容憔悴,历尽了人间酸楚。在这一时期我的父母在自己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积衣缩食,送给姐姐一家救急的粮食就达一千余斤。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历史最沉痛的一年。毛泽东等一批开国元勋先后去世,举国衷悼。此时我的母亲也因患食道癌,病情严重。我的姐姐在母亲病重期间,经常陪伴在母亲床前,因家境贫困,面对病重的母亲无能为力,只能伤心落泪,对天长叹。
由于母亲病危,姐夫也病疼缠身,我的姐姐无法承受这一拔又一拔巨大的压力,她在我母亲去世前一个月悬梁自尽。结束了自己年仅三十三岁的生命。
姐姐的去世犹如晴天霹雳,冲击着我的家人,噩耗传来作为弟弟的我悲痛欲绝、当场昏厥、不醒人事。由于母亲病重在床,我们强忍悲痛,只好把真相隐瞒,谎称姐姐只是摔伤了腿,行走不便。
在我母亲弥留期间,她老人家不知多少次呼唤我姐姐的名字,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让我母亲知道姐姐已不在人世的事实。
我的老父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一生未见过他落泪,只有这一次的丧女之痛、切肤之痛,他老人家背着我的母亲,孤身一人在后龙山上大哭了一场。
在我姐姐过世的二十年间,悲剧一幕接一幕地在我姐家重演,她的六个子女如今只有我的大外甥刘义幸存,其他五个外甥和外甥女都因患癌和服毒身亡。在丧妻、丧子、丧女的无情撞击下,我的姐夫也于二零零一年轻生,随同他的爱妻和五个儿女走上了一条含恨九泉的不归路。
悲痛之余,我忠心地期望我劫后余生的外甥一家能幸福安康,人丁兴旺。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九日(农历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新春伊始,我伴随着慈母的阵痛,带着新春的祥和和喜气来到了人间.上苍安排我这一天降生,也就注定了我喜忧参半的人生。
老父亲四十多岁得子,老奶奶七十多岁抱孙子。全家老少欣喜若狂。他们象众星拱月一样,把我视为上苍恩赐的掌上明珠。
远方的亲戚朋友来了,周围的乡亲叔侄来了,他们一个个都笑逐颜开的向我交母道喜,同时也是用这种朴素的方式欢迎着我的到来。年迈的老奶奶笑了,不善言辞的老父亲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也偷偷地笑了。
我的第一个名字,也就是“乳名”是我父亲请堂叔刘传移取的,他说:“希望侄儿今后能文能武,做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就取名文德。”如今家乡的父老乡亲都是直呼我的乳名。后来上学了,按照家乡当地习俗用辈份取名,我的辈份是“永、远、传、芳、名”的芳字辈。所以我的学名就叫刘芳德。
我的幼年是在父母的羽翼下、在妈妈的怀抱里、在亲人的呵护下幸福地成长的。
我的母亲直到我五岁也舍不得让我断奶。迄今为止我还清楚地记得,每次妈妈从田间干活上岸小憩的时候,我就会跑在地上吸吮着母亲干瘪的乳头流出的甘甜乳汁。想到这里我的心总会惴惴不安。也许是自己年幼无知、也许是自己太自私…….
慈母的恩泽,五年的母乳滋润使我受益一生,我也将感恩一生。
曾记得我五岁那年,在一个隆冬的季节几个同伴上山砍柴,那一天寒风刺骨,我们几个人打赌脱掉了衣裤赤条条的在后山松林里站了半个小时,回家后四个同伴都病了,我却安然无恙。
一九七九年,伤寒病肆虐我的厂区,五百多人染病。我的一家除我外其他的人都被传染。并且都是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跑前跑后全程照顾,我能幸免此难,无疑是母亲赋予我特强的免疫功能。
我小的时候,在大人眼里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会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捡柴、扯猪草、放小猪、推磨碾谷样样都干。那时我的个子很矮,每次磨粉、碾谷时我就会搬一张小凳子垫在脚下,给妈妈搭上一只手,虽然出不了多大的力,但妈妈还是很高兴,炎热的夏天,只要妈妈从地里劳作回家,我就会从井里打一勺清泉送到她的跟前。当我的父亲汗流浃背地回到家中,我就会拿着扇子给他煽风送凉。
我是一个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的人。有一次同村一个人见人怕的小恶棍要打我妈妈,我知道后,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找到这个比我年长个高的小恶棍,把他打倒在地,按到一条臭水沟里狠狠地揍了一顿,从此以后,这个人看到我就绕道走,直到长大后,他还是很怕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动手打人,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的父亲,脾气暴躁,他经常会在我母亲面前发脾气,这时我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母亲这边。护着母亲。久而久之,由于我的举动老父亲也有所触动,后来在母亲面前暴躁的脾气也有所收敛。
我的父亲脾气虽坏,但从来没有动过我一根手指头。其实我也知道,老父亲心里是十分疼爱我的,只是不善于表达罢了。
我七岁上的学,那天我和伙伴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一定要好好读书”,在我后来十几年的读书生涯中,一直没有违背孩时的诺言。
一九六五年,我在油麻中心小学(书院里)小学毕业,当时我们一个班六十多个同学,考取初中的只有三个人,最后被录取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另一个叫刘传星(现在家乡的中学教书),我被分到县立三中(文昌阁)。
第一次离开父母身边到三十里以外的地方求学,我的心情异常兴奋,这一天天刚朦朦亮,我就催着老父亲起了床。由老父亲用一担箩筐挑着九十六斤大米和一床四斤重的旧棉被以及几件旧衣服怀揣十六元钱高高兴兴上了路,也就是这九十六斤大米和十六元钱,支撑着我念完了三年初中,毕业时还退回了十六斤粮票和五元钱。
第一次踏入中学的校门,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在老父亲的陪伴下,我顺利的通过了体格检查,那时身高是一米一三,身重才四十八斤。老父亲把我安顿好后,只嘱咐了几句:“满崽,要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后来没有停留就返回到家中,我把父亲送到学校的大门口,站在那九十八级的台阶上,目送着老父亲的背影消失。心里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报答父母的恩情。
在初中三年学习期间,夏天我只有两条兰布短裤,两件七十公分汗衫。冬天御寒也只有两条用白布自己染成的青色单裤和一件“婆婆夹衣”所谓的婆婆夹衣就是经过几代人穿过、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衣服。衣扣也是开在侧边。象现在一些少数民族老人还在穿的那种款式。
那时在学校用餐也十分简朴,每餐从食堂端回三两米饭,回到宿舍拿出母亲为我准备的坛子腌菜,应付了事。即使没有吃饱也绝不会加餐,因为当时粮食十分紧张,每餐能吃上三两米饭也就十分知足了。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抱怨过家道贫寒。也从来不和那些家庭比较富裕的工矿、干部子弟攀比。因为我深知父母的艰辛和不易,我不能和别人比,也不敢和别人比。
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作为学习委员的我,每次考试每名功课都没有八十分以下的记录,深得老师的器重,第一个学期由于自己表现好、成绩优,我得了三十元的助学金。随后我每期都能拿到三十至五十元不等的助学金,还有五十斤补助粮。在当时这种待遇也只有少数几个同学能享受,当然这里也少不了自己是红军烈士后代这个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