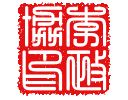妙峰下的诰封夫人墓
此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秩序在军管下已开始明显好转,大姐夫从“五七干校”回来后没有回到他为之工作20多年的公安系统,由物资局再派往“市文物工作小组”工作,用其所长对倒卖出土文物活动进行侦破和打击。
一次周休回家,在大姐家闲聊时,姐夫说起他最近侦查的一起文物案,起因是在古墓挖掘中失落了一件文物,引起了我的兴趣。
姐夫说大凡古墓和一些老的祠堂内总有一些希奇古怪的东西。文革时他在湘阴白泥湖干校劳动,在田间休息看到一条长约
这次侦查的古墓文物失落案子,起因是在湘西北的津市地区修水利工程时,挖开了一座不知年代也不知墓主的老坟。开棺后一看,棺内尸骨早已化成泥土,但出土的文物不少,专家们断代在明末清初。但在清理文物时被当地土夫子盗走了一件流金腰带,查了半年,尚无结果。
姐夫说近期内的侦破很有成绩,线索已确定。倒买之人是本市的文物贩子同港商接触时被捕获的。据文物贩子的口供,他们还有下一步活动,同他们联成一体的土夫子(盗墓者)已通过“望、闻、”等手段发现了地处妙高峰南金盆岭的一座古墓,一旦挖开会有不小的收获,不过盗墓者并没有动手。
我之所以有兴趣是我所在的工厂正处于金盆岭上,周围的古墓好像没有,但荒坟的确不少。如工厂的油库处在离我住地不远的山丘上,那里有不少野坟,无名无主。
夏天白日长,一居室的小间其热难耐,吃完晚饭后我便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外出纳凉。把儿子骑在肩上(长沙人叫坐高马)沿着工厂的外围墙经直向油库的土丘走去。因那上面有不少多年生长的樟树,地势高则风自然要光顾多一些,可乘凉也可让小孩子看看周围的远景。
当我经过几座建筑如同窑洞般的工厂油库时,前面传来叮叮当当的敲打之声,拐过一个小山道,只见约七八个人赤膊着上身,在一坟堆边挖掘,上面的积土早已扒平,下层的土则坚硬如石,钢钎、钢棍、撬杆满地都是,劈去一面的坟墓封土上到处是白色的击打点。
那些掘墓的土夫子全是面生之人,周围也有三五个当地村民在看热闹。我忽然想起大姐夫讲的事,便有意滞留在那里,一边逗着儿子,一边听土夫子休息时的议论。
据他们说已接近了棺材,只能用人工的方法解决,如果用炸药不关会全功尽弃,还会惊动军管会。而那坟下层的填土是通过特殊处理的,几乎没有看到卵石,有点像“三合土”但比它更瓷实,我看到他们对棺材的位置计算得很精确,开挖的手段也很有讲究,在劈开的封土断面上开槽,然后冲击槽中的土块,达到省工省时的效果。我无法分清他们之中谁是主要策划者,地上没有祭祀的物品,也没有“洛阳铲”之类的盗墓专用工具,是乌合之众,还是使力的杂工,是有备而来还是偶获机会,一切都有点神秘。
在他们挥汗如雨的劳作中已暮色四合,看土夫子们的架式只怕要连夜干了。俗称: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无月之夜是不法之徒干见不得人勾当的最好时期,而今夜,肯定是月明星繁,因小道两侧的树叶纹丝不动,暑气尚也未完全散开。
一个无风闷热的夏夜里,朗朗星空之下一场罪恶的盗墓行动就会这样开始。我有几分不信,只想看个明白。但儿子有些吵闹,不得不回家。
肩负着儿子拐过山丘后,敲打之声也渐渐地消逝在夜色之中。
第二天,关注此事的我便一大早跑到了挖墓之地。看到现场上空无一人,大量的挖掘工具七零八落散了一地,晨风不时掠过荒坟外的杂树和草丛,连鸟鸣声也显得特别的悠扬,一切都是那样的平和,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只有那相嵌在高约
土夫子们一晚的收获已见成效,荒坟断面的棺木已裸露出尾部的端面,但还是被四周特制的泥土包围得严严实实。
透过棺材端部黄白相杂的泥砂,描金的云龙图案时隐时现,其尾部的规格要大于我所见最大棺材的头部(《长沙文革记事》中所述武斗中惨死的王师傅因尸体高度腐败,造反派在厚葬中所用棺材是我所见中最大的),这无疑是姐夫所说的有关盗墓者将要挖掘的无名坟墓。
何时开棺,没有人告诉我,挖墓者是否休整后卷土重来,还是暂搁在这里等待高人和时机,一切都是个迷。
无奈快到上班时我还不见盗墓者的踪影,只得偷偷告诉了我的徒弟,要他守在附近,一旦有消息马上到车间来找我。
上午十点多,徒弟满身大汗跑来说:“来了!来了!棺材端盖已被土夫子用四齿锄撬了下来,挎下了好多石灰,还叶(刺激)了两个人的眼睛,快去看!”我听后忙放下手中的工具,同他一道跑向厂外的山丘。
烈日当头,晴空万里,小山丘四周站满了看热闹的村民,开棺之处闹成一团,有十多人围着那劈开的古墓断面在争论不休。
我好不容易挤开围观的人想看个明白。只见黑的木炭、白的石灰,黄的泥砂再加上汗水把盗墓者们的脸和全身染得如同戏台上的小丑一样,疯狂让他们失去了人的理智,一场罪恶的掠夺在光天化日之下用争吵的方式进行着。
围观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在注视着这一无政府行为的发生,谁也不想多事,红了眼的掘墓者对阻止他们的人不知会采取什么手段,除了军管会谁对他们的行为都无能为力。
盗墓者清除了棺木端面的填充物后,露出棺材四周崭新的松木色,还飘散出淡淡的沉香味。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露了出来,引起了人们一阵惊呼,“是女尸,好细的脚。”没有人性的盗墓者们争先恐后直奔那古墓断面的开口,有抢夺女尸脚上鞋的,有在两脚外侧掏摸的,也有顺着女尸的双腿向上摸的,怎奈棺木开口不能容几人同时干,陪葬品都想要还能不打起来吗?
于是,边骂边打,撕扯死者衣物乱成一团。这时我大约明白了组织开挖者的目的是收购,盗墓者只是比谁的手粗、手快拿得越多的无组织的乱挖、乱抢一通。
女尸在棺内包扎得十分严密,脱下一只小绣花鞋后,包脚的白色丝绸散落几尺长,但整个尸体如嵌在棺内,纹丝不动。有人用四齿锄头和撬棍狠挖棺材底部的巨木,两侧的镶板也如法炮制,折腾了一阵后,再好的棺木也经受不起如此敲打,终于有些松动。
接着,第二轮哄抢又开始了,因尸体搬不出棺材,撕扯包尸的几层缎带时,搞得四周如雪片在天空飘散,多年封存的丝制品在烈日下很快风化,变色。
这时,一条葱绿色的百折长裙转瞬间退色变白,在盗墓者的撕扯中丢到我的面前,裙边上的英语字母清晰可见,我在辨认中发现仅是一种图案,而不是文字的含意,否则,我即可判断此墓年代不会久远。
很快,尸体的一条腿又被他们生生扯断抛了下来,扯断处有点像经风吹过的肉,因多年失水的结果有些干,但肌肉还很有弹性。当那条腿落地时惊跑了不少围观者,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搞得冒明堂,咯是分尸呀!”一位盗墓者用手指着我喊叫着:“关你卵事,看不下去,你就滚蛋!莫搞得老子宝气来了,打人?”年青的我本想回应几句,旁边一位文质彬彬的老者用手拉了我一下说;“算啦,说也无用,会遭报应的。”
奇怪的是那女尸好像有意同他们作对,硬是在棺材内拉不出来。这时,有一经瘦之人干脆带着一条麻绳从端口进入棺内,绳的一端系着自己,另一端系在尸的头颈部,面对面用自己的力把女尸拉得坐起来,(外公同我讲过那叫捆尸索,不是一般的绳子,绳上动了咒,有些明堂)由于坟墓葬得好,尸体保存如下葬时一样,只是干点,这一拉,不但未断,还像被子一样卷了起来,真是奇了。
盗墓者们一哄而上,把女尸从头到脚翻了个遍,我们这些人也被他们赶得远远的,所有的陪葬品被洗劫一空,包括棺内的。他们拿走了一些什么宝贝,我也无法知道。有可能是分脏不匀,其间相互又打了一大架,头上的血也打了出来,临走时还不忘教训我们说:“谁嘴多,就找谁算帐,不信,试试看!”接着,盗墓者们收拾工具后便一哄而散了。
老天会真的会有报应吗?我不知道。只记得,他们离开时,晴空突然转阴,一声闷雷响过后,夏日的阵雨从天而降,豆大的雨滴打得四周一片响,看热闹的人被突来的雷阵雨惊得四散一空,只剩下我,徒弟和拉我手的老者三人,躲藏在一棵硕大的樟树下相对而立。
路面刚好打湿,则雨过天晴,地面向上升腾的热气一个劲地挥发着,让人十分难受。奇怪的是抛在地上的女尸虽然失去了一条腿,在内长裙的掩藏下显得十分完整,卷曲后的尸身又舒展开来,静静地躺在地上,在热气的升腾中没有一丝尸臭味,地上的古人和站立着的今人相对无语,是时光倒流还是长生不老,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搞笑。
大雨过后的小山丘上的植被青翠欲滴,蝉又震翅高鸣,能让人感受到只有大自然能包容一切,几个小时前的罪恶行为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四周又恢复了往日的安祥。
我们三人这时才走近掘墓的现场,仔细查看那怪异的女尸。其身长不会超过
在我细观时,同行的老者已叫来了两位当地的村民,找回了那条丢在远处的断腿,想连同尸体一道设法在小山后掘坑掩埋。
我年少无知,当时未曾想到这一点,对老者的行为特感动,连忙呼唤徒弟一同加入,结果在取土时又发现了一重要物证,即一块汉白玉墓志铭。
是盗墓者们在拖出棺材翻找陪葬品时,在棺材底部的砂土中找出了一块约两平尺的石板,认为无用,便用撬棍将其掀至荒坟下的泥土之中。
我同老者借用村民的锄铲除了石块上的泥,当露出了白洁的本体时,老者惊呼道:“好家货!汉白玉的,是一块墓志铭”。这时我也明白了同我一起看热闹的老者不是平常之辈,俗语称:凡事问三老,有他在我可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连忙掏出香烟递上去叫了一声:“老伯!我们听您的,您说如何搞我们就如何做。”
“先洗洗看,肯定同墓主人的身世有关。”
我叫徒弟从附近池塘中打来一桶水,把石块上的余土洗净,清晰的石刻字全部显露出来。全文约百十余字,文言文,内容不大好懂。现在约记得开始和结尾的句子:“皇清诰
我把我的推测告诉了老者,得到了他的基本认同,而对不懂的请他给我讲明。老者的兴致很高,在香烟的进攻下向我尾尾道来:从墓志铭全篇内容看,这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女子,生于江宁织造官府人家,同当朝同治皇帝有一定的亲缘关系,自小饱读诗书,为人贤惠,貌美,二八年华嫁到长沙,因难产而死,时年不足十九岁,如果寿长还活着的话也就120岁左右(当时公布的世界最高寿者是丹麦人女性124岁),老者还讲到:清朝大凡皇清诰封都有品级,而此女则无,葬的规模同其地位很不相符,实在有些让人困惑,但从其棺木和封土层看还是划了不少功夫的,莫说百多年前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约30多年前,长沙城区躲难的市民也只跑到城边冬瓜山去躲避日机的轰炸,而此地离冬瓜山尚有十余里之距,肯定是城市外的偏僻之处。把这么大的棺材抬到此地,翻山越岭困难可想而知,不是大户人家实难办到,正因葬得好同时也得益于风水才有百年后尸体不烂的较果。只可惜处在动乱的年代,又碰上了一群疯狂的盗墓者让她抛尸露骨,太不应该。
听了老者一方说道,我对其已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只是对墓志铭内容的初步理解就能说出个名堂,不管说的和推断的准不准确,足可让我听得如痴如醉,浮想联翩。
这是一位四处云游的逍遥之人,无论我如何打听,老者都没有告诉我他的名性和单位,将女尸落土后便走了。
回家后的我心绪难平,我觉得要做几件事来安慰这位百年前的诰
我把第一消息告诉了大姐夫,尔后的几天内参加盗墓的人全被市文物队找到,也让他们尝试了做阶下囚的滋味,所有陪葬品基本收回国库。
我把第一消息告诉了工厂军管会,要他们派人把那块汉白玉墓志铭收起来作地名普查用,后据说没有收到,被当地无知的村民连同死者撕扯下来的物件一同抛到了山下的深溏中,无法打捞,不了了之。
三十多年后,工厂生活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兴土木,建成一大型社区,在征求社区名称时,我把“德乐”二字的来历告诉了他们,终于在一大批应征者中,选取了我的提议,取名“得乐园”。也完成了我多年来的夙愿。
关于这座古墓,当然还有一些小道新闻,当文革结束后两岸关系的对峙发生变化时,有消息说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