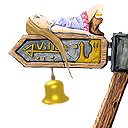图为打工诗人郑小琼
——————————
贫困时代的诗人
(牧歌)
想写一点关于诗人的文字,突然想到了“贫困时代的诗人”这样一个标题,这很吻合我对于诗人境遇的印象。虽然经过查询,知道这个标题已经被人写过了,我仍然想就此谈谈自己的感慨。我当然不会对社会的繁荣与进步熟视无睹。但是我要说的是诗人——一个在几乎每天都在产生着财富神话的国土,却依然坚守着一份清贫的群体,一个在物质与精神的取舍之间痛苦挣扎的群体。
我刚刚拜读了凌翩先生关于采煤工人陈援华的诗作的介绍。陈援华是一位“从耕耘土地到采掘煤炭的农民工;是一位在湘中的一座矿山“堂堂正正”的花名册上,找不到自己名字的外包工;是一位“懂得煤层的蕴藏位置”“同时也懂得诗歌的位置”,在地心不懈双向掘进近二十年的矿工诗人。”无疑,这是一位来自贫穷王国的诗人,他在窘迫的生活境遇中,在地层的深处,在可以燃烧的矿石中,寻找着自己的诗歌,他的生命也因此燃烧。
了解一下当今的诗坛,如陈援华般来自打工一线,坚守着清贫却执着于诗情的,还真灿若星辰。
许强,中国第一份打工诗刊《打工诗歌》的创办人。1994年大学毕业后,兜里揣着36元钱,从四川来到深圳闯天下。许强写下了许多诗歌,《诗刊》、《星星诗刊》、《绿风诗刊》、《中国诗人》等国内有名的期刊纷纷发表了他的诗作。在简陋的宿舍中,他用一支笔雕刻着中国南方打工者真实的形象。在平淡的生活中,写作打工诗歌成了他生活的唯一乐趣和享受。郑小琼,这个常常穿着半旧碎花短袖衣,黑布鞋,素面朝天的瘦小女孩,总是低着头嘿嘿地笑,和城市家政市场上的小保姆没区别。其穿着和打工身份与著名诗人、人民文学奖获得者形成巨大落差。许强和郑小琼都经历过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日子,至今仍属于贫困一族。
前不久,网络上爆出一条新闻:一湖南诗人期待被富婆包养来实现写作理想,得到一名重庆富婆级女作家的青睐。女作家表示会和该诗人签订一年的“包养”协议。不久又见《北京晨报》消息:38岁的河南诗人张少言作出大胆举动,他写着“卖自己”的牌子当街展览,希望有伯乐能够相中自己。张少言伤心地说,这十年来写诗带给他的是穷困和潦倒,他希望此举能改变他窘迫的境遇。
贫穷与多种困惑,一直是诗人群体挥之不去的梦魇。以致频频有诗人因此早夭,这其中不乏诗坛骄子。如写下“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寻找光明”名句的顾城,写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名诗的海子。就在上个月的10月4日凌晨,长居云南昆明梁源三区的湖北籍年轻诗人余地,在家中自杀身亡。据其生前朋友介绍,余地有一对不满3个月的双胞胎儿子,其妻身患重症。有人指出,经济压力和在文化以及精神层面的巨大困惑,是这些诗人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诗人的职业特致和精神特致,命运使得他们必须承受来自至少三个方面的精神压力。一是物欲时代文化沉沦带来的生存价值评判的错位造成的强烈的失落感;二是诗歌创作的职业特质导致的贫穷;三是来自诗歌本身的困惑和寻找突破契机的巨大精神压力。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诗人尚有较多的机会接受国家机器的眷顾,工农兵诗歌还曾戴上主人翁诗歌的光环。那么,自主经济时代的诗人,则几乎失去了任何体系的眷顾,他们因劳动成果变得几乎一文不值而倍受贫穷煎熬,他们一边抒写着上帝的箴言,一边为五斗米折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诗人,财富时代倒真成了一个贫困的时代。著名诗人伊沙写过:“饿死他们,饿死狗日的诗人”的著名诗句,我以为,这不仅仅包含对诗人的某种批判,更是对诗人境遇的哀号。
中国文化因诗开始,一部《诗经》演绎了从蒙昧走向兴盛的文化历程。然而,当我们在享受经济文明的同时,传统文学价值的丧失却痛如针刺。海德格尔认为,当整个世界陷于某种危机境地之际,唯有真正的诗人在思考着生存的本质,思考着生存意义。诗人以自己超乎常人的敏锐,以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以自己对于存在的形而上感知,以自己诗的追寻蕴含着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并且把对终极目的沉思与眷顾注入到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中,去洞见生存的意义和尺度。唯有真正的诗人才可能不计世俗的功利得失而把思考的意向超越现象界的纷纭表象而去思索时间,思索死亡,思索存在,思索人类的出路。
财富时代的贫困诗人,我们该如何眷顾他们?这是悬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大厦上的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