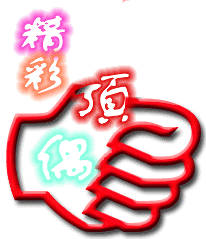一九七五年我们过了一个热闹年.那年我们喂了两头猪,小猪七十多斤,大猪有一百八十斤。在这偏远的山村,一百八十斤的猪算是大家伙了,我们决定杀这头猪过年,留下小的喂到明年送“派购猪”。
下放到这山村十年了,基本上混出了点名堂,七四下半年我当上了民办教师,翘妹子当上了大队赤脚医生。比在生产队出农业工要“土松”得多了。细牙子多,口粮也多,当教师和赤脚医生的工分都比较高,年终分红还进了一百多块钱。
记得杀猪那天正好离过年还有二十天,我们实在喂不下了,两头猪每天要吃两桶食,天冷饲料也难寻,反正迟早也要杀的,主意一定,决定下午杀猪。
队上的两位副队长就是杀猪能手,一听说下午要杀猪,可把那些队长队委们乐坏了,下午准备到田冲去检查积冬肥的情况都不愿去了。大家都来帮忙,烧水的烧水,劈柴的劈柴。磨刀啦,借屠盆啦,反正把猪杀了肯定有餐饱肉呷,我还让翘妹子去代销点打酒去了。
水一会儿就烧开了,大家一齐把猪从圈里拖了出来,提的提尾巴,按的按脚,一刀就捅翻了,还接了一大盆猪血。这时,忽见公社
王干部(在我们队上蹲点)朝这方走来。本来,他已经安排好队委们下午去田冲里检查积冬肥的情况。现在大伙都在帮 我杀猪,他心里肯定有气。去年我队来了一位黄干部登点,他是林学院毕业的知识份子干部,在我队干了一年,把生产队屋前屋后的大古树都下令砍倒了,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在这里发起,田冲里都种上“双季稻”。全队人辛辛苦苦累了一年,结果只增了几千斤扁壳谷,他本人到捞了政治资本------光荣加入共产党。
今年又调来眼前这位王干部,他是长沙师范毕业的,戴了一副宽边眼镜,人称他“王眼镜”。这王眼镜脾气特别怪,在公社和公社的大多数干部都搞不来,就连从地区派来的宣传队队长,他也同他吵过一大架。那位工农兵干部段队长就因开会时讲了一句“鸡巴毛”就让他王眼镜钻了空子,他写了几张大字报“鸡巴毛何解”?王眼镜会写会分析,他从三大纪律讲起,从八项主义里去分析,弄得那位段队长下不了台。
今年他又调到我队来登点,他整天不干活,就是爱训人,开口就是“资本主义”“阴谋诡计”那一套话。每天晚上都要召开会议学习,听他讲当前的大好形式。他操着那口“湘乡“口音,不管社员们听不听得懂,他照样地讲,照样地念文件。今天他肯定又要训人,因为队长队委们都在我这里帮忙杀猪,检查工作都不愿意去了。
果然不出大家所料,他走到我们面前:“今天下午的检查工作不去了,在这里杀猪,搞这些资本主义。”
大家都不理睬他,专心专意的修猪刮毛。他更气了,两边嘴角上立刻起了白泡子。他走到我面前:“你一个知识青年,在这里扎的什么根,尽搞这些资本主义,影响学大寨。”
我本想还他几句嘴,但想起今天杀猪是一件好事,万一和他吵起来扫兴。于是忍了忍没有还他的嘴,便走进屋里拿东西去了。只听见他在骂:“你们满脑子的资本主义,革命工作不去干,你们要好好地“斗私批修。”
大家还是不理睬他,他见我走出房门,又冲到我面前:“陈晏生,你要对今天的事情负责,晚上学习你要作检查。”
我望着这迂里迂气的样子,又好笑又好气,我还是忍着不做声。大家已将猪修好,只听操刀的副队长一声吼:“站开些,要动手开边了!”
大家也一齐喊:“开边了”!便将修白了的猪一抬而起,挂在了早已准备好的横杠上。王眼镜被挤到弯角里了,这一下他觉得自己太孤立,站在旁边有些尴尬,便气呼呼地走了。
猪一下就开成了两边,大伙人帮着挤肠子,洗肠子,煮猪血,刮肚子,忙得不可开交。
社员们都围拢来看热闹,都夸我们的猪喂得壮,喂得大,肉一定好吃些,有一社员提出来借几斤肉吃,我答应了。谁知道这一答应个个都提出来要借几斤。来山村十年了,个个都有面子,何况大家都开口,借一个不借一个讲不过去,我和翘妹子商量后决定每户都借上几斤。这一下可好了,一阵工夫就借走一边猪。要得呢,杀猪就是喜事。尤其是这大肥猪,大家尝一尝也好,反正过些天都要杀猪过年了。跟着就能还回来。
开饭了,我请来“干亲家”(原大队书记)掌瓢,我让他炒了一大锅颈圈肉,炒了那笼小肠,煮了一大锅猪血。十几个人围在火塘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吃得好开心喔。
队委们个个都吃得酒醉饭饱,会议室的王眼镜吹了三轮哨子,我催他们快去开会,我还要忙着检场。夏姐还要帮我做香肠。做米粉子肉。。。。。
会议室里时而传来一阵阵笑声和喧闹声,我晓得,近段日子王眼镜天天晚上招开会议,他们早就不耐烦了,今晚喝了这么多酒,肯定
撒酒疯。
第二天清早我挑着水桶正准备去担水,王眼镜早已等候在门前:“你为什么拿那么多酒给他们喝?我看你这家伙别有用心。”
这一下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把肩上的水桶望地上一放,大声吼道:“你一开口就骂人,你是什么家伙?”
翘妹子从房里冲出来:“你是什么干部?你凭什么骂人?”说完冲到他面前,双手拍起巴掌:“你怕我们是四类份子,随你来骂,随你来训哦!”
“你在公社里和干部爱吵架,又爱骂人,下乡来你哦实还不改?天天骂人,你算老几哦?”我说着,冲到他面前。翘妹子也跟了上来:
“你读了十几年的书,是从屁眼里读进克的摆?”
我两口子一个一句指着他鼻子骂,把他逼到大门角里,他可能是被我们突然爆发给吓住了,退到门角边一句话都说不上,只是用手指着:“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
这一下围来好多社员看热闹,大家都在帮我们的腔:“各是什么鬼干部,天天就只晓得骂人。队上的人个个都被他骂到!”
“他那天还骂了我,还骂我的爹爹,碰到我奶奶又骂我奶奶。”妇女队长好气愤的说。
大家你一句他一句,这平时会骂人会训人的王眼镜居然答不上一句话,灰溜溜地走了。
翘妹子还不甘心,追上去说了一句:“你回去过年咯,帮你的婆娘做点事咯。”
我又加了一句:“天大的事明年开春再说,现在要过年哒。”他头也不回,气冲冲的走得好快!
第二天他真的打起背包走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这个队上的正气树不起来-----”
王眼镜走后,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方案很快出来,大家分了红,家家户户都忙着杀猪,到了三十那天,大家借去的肉都一一还来,我那火塘上又挂满了肉,我望着那一串串的肉,心里乐磁磁的。
这时,我猛地想起七三年的一桩事:那年我和翘妹子带着两个孩子回城,本来打算过了年再回乡。谁知道那天晚上一阵踢门声把我们惊醒。我妈妈把门一开,闯进来一伙人查户口,为头的那位居委会主任卢子英,垮起个脸块,只问我们什么时候回乡?一位操乡里口音户籍质问我们是否报了户口,什么时候回乡?不要逗留城市。我当时真的气得要死。想当年,我们下农村时,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好光荣。没想到,我六年才回来探下亲却遭到如此辱骂。心里好不是滋味啊。我那时恨长沙,恨长沙的这些畜生们,尤其是那位卢子英,她的为人我最清楚,没想到这号女流氓她也能当居委会主任。还有那位操乡里口音的户籍,明明自己是乡里人,偏偏可以安排到城里来工作,还来催我们到乡里克,真是岂有此理。我想起儿子已有三岁了,不能让他小小的心灵受惊吓。我们一气之下便回乡了。回到乡里比城里心情好,只要自己勤劳,一样的混得不错。而且我们还可以直起腰杆做人。
想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的一切,我今年一定要热热闹闹过个年,我杀鸡,杀鸭,蒸扣肉,蒸粉子肉,炖猪腿,炸肉丸,闷香肠,炒肉丝,还把社员送给我的“穿山甲”肉也炒上,足足办了十几个菜,铺满一大八仙桌。晚上我又叫来“干亲家”陪我喝酒,三个儿子围着桌上边转,一个个笑得嘴都合不拢。真的痛痛快快过了一个三十夜。
三十二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每到过年我总回味着那年过年,那是我终生难忘一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