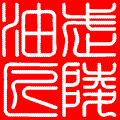水漫南洞庭
大湖之南沅江县,水网密布,河汊纵横。一条大河,源自广西越城岭北麓,穿过雪峰山后称为资水,挤开丘陵,闯入沅江,汇入八百里洞庭的怀拥之中。我的生命曾经在那里驻足羁旅。
1969年6月,农历5月里。资江河畔,岔角生产队。东风染尽三千顷,折鹭飞来无处停,田野一派秀丽景色。早稻青禾分兜、拔节和孕穗,“晒田”的时候到了,但却碰上了连连梅雨。
生产队长宣爹带着我,一把锄头一只窝锹,黄斗笠棕蓑衣,斜风细雨里,赤脚田埂行。这时的稻田需要湿润但不能浮水,我们挖口子抽沟排水。
歇气时,宣爹望天算一卦:“五月十三落了雨,湖里没了洗脚水。”用沅江话念起来特别押韵。我问是什么意思,宣爹告诉说,阳历6月初早早地下雨,今年肯定就会天干。
没想到这一卦不灵。6月中旬天幕如裂,暴雨倾盆,持续不断。资水率先发难,益阳进入主汛期。紧接着湘水、沅水、澧水兴风作浪,四水汹涌奔腾猛灌洞庭湖。沅江县在洞庭湖区的地势如锅底,立时浸在水里。
洞庭湖区乃“天下粮仓”,但是湖区的农户家家都缺粮。6月底本是希望的时月,“快哒块哒,有顿饱饭呷的日子就快来哒。”堂客们对围着灶台哭的小崽子都这么说。青黄不接的日子快熬到头了,扳指头划算,只等半个多月就可开镰。
可是,现在等得下去么?百亩大田渍溺水中,青禾拔穗水面摇曳,仿佛在哭号着“快快收割”。宣爹望着心急火燎,还等什么,再等谷子就会烂到田里去。
生产队里开黑会,决定提前开镰抢收青谷,就收就分配,先搞点呷饭谷再说。那几天的紧张劲,就像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抢粮食,一下就剃光了三十几亩禾田。
这么大的动静,想不被发现都不容易。上头马上紧急刹车:凡是没有转黄的禾田一律不准开镰。道理说得我都明白,那青谷刚灌浆尚未成熟,一收不就肯定减产么。气象广播说了,进入7月后,肯定会有一段持续的晴好天气,等到那时谷熟开镰,丰收肯定在望。
那天晚边子,宣爹匆匆过身,我一把拦住开乐心,戏弄他打的卦不灵,再要他算算气象广播灵不灵,宣爹笑言:“广播就是讲白噻。”“讲白”在沅江话里就是扯淡的意思,“广播”在沅江话里恰巧又与“讲白”谐音,这老小子会幽默。他扯起脚性急要赶去开会,那神态洋溢着一种向往,到公社开会就会有顿饱饭呷,干部哪个不望开会。
第二天清早,只听见柴油机震天吼,出门看见宣爹忙上忙下搞不赢。一夜不见,这老小子就变成个鬼回来了。眼睛血红嘴皮起泡,手杆子上还有两条麻索印。
宣爹的女春伢子哭诉说,昨天晚上宣爹赶到公社里,刚上饭桌抓筷子,就被喊出来进了武装部,进门就听喊声“站哒”,接着一顿吼起骂起,还绑了一索子,只问收了好多亩青禾、有好多斤谷分到了社员屋里。违抗县里精神不说,产量冒报、公粮征购粮冒交、种谷冒留就私分,咯还得了,反上天了。最后认罚5000斤征购粮任务才收了场。来去一夜粒米未进,还挨了骂绑了索子。宣爹顿足叹曰:“人作孽比天狠哩”。现在的岔角,是浸到一个满水的脚盆里了,只有性急排水干田不烂谷,看保得住几成熟谷进仓。
6月底往7月初转,雨歇阳光照。空气中机声轰鸣,机油味燃烧,沅江境内所有的垸子都在赶排渍水。那柴油机全大队只有一台,十个生产队都抢着要,成了俏货,柴油机手要好吃好喝地招抚,米饭要一粒一粒的不成坨,肉要大块大块熬出来的不掺假。有一份报告总结说:全公社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在县委、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刹住收青谷的歪风,奋力排尽渍水夺丰收。
艳阳天下我戏说宣爹,咯气象广播冒讲白呗。他阴着脸说:“老天报应在后头哩。”我说你老就是个乌鸦嘴,不但卦不灵还尽讲晦气话。那老小子无心答白,只是叹气。
没想到大不幸,宣爹的这一卦算准了。7月,长江主汛期到,洪峰迭起,长驱直下,汹涌地扑向洞庭。洞庭湖的水位猛涨全面抬高,仅次于1954年的历史最高水位,而且在严重顶托下居高难下。
宣爹打比方,先前是一盆水浸没了脚,现在又有一大盆水顶在了脑壳顶上。我问还有什么办法,他回一句“要是有垸子垮就好了”。这话说的缺德但道理在,洞庭湖区围湖造田,大大小小的垸子不胜其数,蓄水面积越来越少。大水来临之际,就只望别个的垸子溃决,行洪泄洪蓄洪;保得自己的垸子平安。
这时候站在堤上看,垸子外水天茫茫,大水压境,是为涝;垸子内的房屋、大田都浸泡于水中,盈水排不出,是为渍。队上的劳力大部抽到资江大堤上防洪抢险,双抢的事丢给了一些年老体弱的和伢婆细崽。早稻水中浸泡高温蒸煮,一把一把从田里捞上来时有了腐臭气;晚稻几乎没办法插下去。仅存一点微薄的希望落了空,柴油机的轰鸣声停歇了,垸子里末日般的死寂。天漏地渍涝,这就是1969年的沅江水患,它锐割深刻在农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