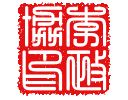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 http://news.tom.com 2003年01月08日10时42分来源:中国青年报吴湘韩 |
1月6日,长沙。大雪纷飞。正在家里焦急地等待官司判决结果的陈靖荣,接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要他去取判决书。
以下内容为程序代码: <SCRIPT src="http://news.tom.com/script/ad.js"> </Script>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http://ad.tom.com/zhf/pip/newspip.js"> </script> 陈是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退休摄像师。他一看判决书上的日期,大为吃惊:“判决书落款2002年9月18日,怎么三四个月后的今天才给我?” 1 “下海” 前几年,电影业受到了各种娱乐形式的冲击,尤其是国家对制片厂实施“断奶”后,制片厂无一不在风雨飘摇中苦熬。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潇湘电影制片厂把生产人员推向市场,谁能找到钱谁就能拍片,不管是否有任务,职工每年向厂里交纳劳务费,厂方才能发放工资。 该厂电视剧部还专门颁发了《摄制组工作暂行规定》:“制片主任或制片人是摄制组的行政领导和生产的组织者,同时又是掌握该片资金的使用者,或者同时又是全部资金的筹集者,必须对该片的摄制、财务送审、送播、组织发行、销售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 过去总以为只要把本职工作干好就可以了的陈靖荣,迫于形势不得不四处寻找片源和财路。他和著名军事家黄克诚是同乡,对黄克诚正直不阿的人格极为推崇,立志把黄老的形象搬上荧屏。他找到该厂的一位负责人请求拨点经费,但该负责人回答:“《黄克诚》剧(以下简称《黄》剧)恐怕难搞成,劝你不要搞。” 陈靖荣并未死心。1992年回老家永兴县过春节期间,他找了县里的领导。对方当即表示尽力给予支持,并前后给了8万元资助。 靠这笔钱,他启动了《黄》剧剧本的创作、策划:搜集、提供了关于黄克诚将军的生平资料,并提出了编写《黄》剧剧本的主题和思路,审定剧本大纲,安排编剧实地考察,并承担了来回路费等考察费用。同时,陈靖荣还亲自选定修改剧本的人选,并根据黄将军家属和部下等人的意见,指导作者将剧本先后修改了14稿。 1994年5月22日,陈等3名策划人代表与编剧汤炜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作者酬金为4万元,剧本版权归“策划人”方。 陈告诉记者,由于忙于此事,1994年没有完成厂里规定的创收任务,厂里全年只发了工资的70%给他。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几次送审、修改,该剧本终于在1995年4月通过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电视办公室的审查。 此时,以前给他冷遇的某负责人转变了态度:“小陈,我可以给你出出主意。” 从1995年到1998年4年中,陈继续做了大量工作,如主持剧本的后期修改、剧本送审、剧组的筹建、导演的聘请借用、演职员的选定、起草呈送有关部门的报告、选定外景地、剧组经费的预算和管理等。 1998年2月,《黄》剧正式开机,同年6月关机。 其中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潇湘厂在1998年7月给有关部门的报告中曾这样谈到:“该剧剧本创作6年,改写了7次,正式送审3次,批复3次,也是我厂所拍同类题材电影、电视剧没有过的。” 这份报告提及一些“功不可没”的人士,但没提到作为《黄》剧发起人和组织者的陈靖荣,并说他是“从1993年起参入《黄克诚》剧策划组工作”的。 在该剧的署名问题上,潇湘厂只给陈署名为制片主任(排第二位)、剧本策划。 但据陈初步统计,在制片期间,他为该剧出差的天数高达367天,远远高于其他任何人。同时,由陈靖荣本人直接筹集到的资金也占总筹资的四分之一,达104万元。 就是在这份报告中,最后写到:“为了加强领导,由副厂长××代表挂帅,全权代表厂长对《黄克诚》剧实施领导。” 2 分配 在策划的前期,陈靖荣曾经就利润的分配问题起草了一份协议,提出了“三、三、二、二”制,即在《黄》剧有利润的情况下,湖南 A部门得30%,潇湘厂(使用了其许可证)得30%,策划者(具体筹资者)得20%,摄制组得20%。他要求签订协议,该厂一负责人说:“你就是制片主任,你管经济。” 但此后,陈得到了一份潇湘厂与 A部门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规定:“本协议书一式三份, A部门、潇湘厂、策划组各执一份”(但仅有潇湘厂、 A部门两方的签字,没有盖公章)。 该协议约定,《黄》剧由湖南省纪委和潇湘厂联合拍摄,策划组具体实施。 A部门在拍摄过程中的职责是“向上级申请拍摄资金”;潇湘厂的职责是“负责具体的拍摄工作”;而策划组的职责则是“负责编写剧本,筹集资金(物资)”,并协助拍摄。 还约定,《黄》剧版权属于 A部门和潇湘厂两家共有,将《黄》剧利润分成比例定为:潇湘厂40%, A部门40%,策划组20%。 1998年11月8日,《黄》剧经中央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电视办公室审定通过,同意修改后播出。 1999年1月21日,潇湘厂将《黄》剧转让给中央电视台影视部,转让费为104万元。 A部门“领走”34万多元;策划组得17万元(陈本人在其中分得4.6万元)。 1999年1月,中纪委办公厅同意组织《黄》剧的发行。 该剧1999年4月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后受到好评,先后获得1999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19届“飞天奖”二等奖、湖南“五个一”工程奖、省广播电视厅优秀电视剧奖。上述颁奖活动陈靖荣均未被允许参加。 陈说,按照部门制定的《关于电视剧和录像片集资收费管理办法》,“向社会集资的摄制费,集资人可提取10%至15%,最高不超过20%的集资活动费用;争取政府专项拍摄资金投资拍片的,可提取5%的集资活动费用”,为《黄》剧筹资这么多,但他从未提过成。 3 争议 给陈的酬金,与在剧组仅工作几个月的人一样多。陈认为,这不合情理。因为他是《黄》剧的发起人、组织者及执行者,付出了6年多的艰辛劳动,根据《劳动法》应合理计算他的酬金和劳务费。 陈靖荣还“固执”地认为,策划组应该拥有《黄克诚》剧20%的版权,片头应该给他署名“总策划”或“制片人”。潇湘厂瞒着他向中央电视台转让《黄克诚》剧的版权,也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他说,自己多次咨询了版权部门、湖南部分高校的一些版权方面的专家,越发坚定了信念。 从1999年开始,他多次上访讨说法,但“没有任何人给我说法”,有的领导甚至说他“争名争利”。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想起了法律。在湖南先后请了三个律师,结果“搞了半年多,连案都没立成”。 后来,他背上两大袋五六十斤重的材料,到上海找到专打知识产权官司的著名律师朱妙春。因《黄克诚》剧曾在上海播放过,陈就在上海起诉潇湘厂和 A部门。 2000年12月,此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休庭后,通知2001年2月21日第二次开庭,后来法院给陈打来电话说暂缓开庭。同年7月19日,上海方面将案件移到了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陈见久未开庭,经常到法院问开庭的时间,对方总是这样回答:“要领导定。” 于是,陈又走上了上访的道路。直到2002年8月22日,长沙市中院才开庭审理此案。 法庭上,双方唇枪舌剑,《黄》剧是否是陈的职务作品成为争议的焦点。 陈及其代理人、上海市天宏律师事务所朱妙春律师认为,陈是《黄》剧的制片人。其根据是,在该剧本审查通过之前,根本看不到被告的“领导”和“参与”,也没有资金上的支持。只是在剧本经反复修改通过审查之后,两被告才“主动领导,积极参与”,于是功劳成了两被告的。在后期,在资金方面起主要作用的仍是原告。 被告潇湘厂却认为,《黄》剧的经费,是以 A部门和《黄》剧领导小组的名义向财政部门申请和向有关单位筹集的,具体和拍摄工作由潇湘厂负责实施。该厂和 A部门是《黄》剧的制片者。 而陈靖荣是该厂的职工。他一直是用潇湘厂或湖南省纪委的名义拉赞助、搞策划,《黄克诚》剧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他拍《黄克诚》剧的所做所为,都是一种“职务行为”。此外,根据《广播电影电视部影视制作经营机构管理暂行规定》,个人和私营企业原则上不设立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原告从法律上讲也不可能成为《黄》剧的著作权人。 A部门也认为,在资金筹措上,原告是以被告的名义为该剧筹措摄制经费,所筹集的资金也是存入领导小组办公室开设的单列账户,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对《黄》剧进行过投资;在拍摄该剧的整个过程中,原告行为是代表两被告行使职权,是在两被告组织下负责电视剧的具体工作,并领取相应报酬,原告不需要承担政治、经济风险,《黄》剧的送审、制作、发行也是由两被告完成的。 对此,陈的代理人认为,职务行为是员工依据劳动合同所明确规定的具体职责范围内所从事的行为,或者是主要利用(无偿)单位物质技术条件的行为。而陈的本职工作是摄像。在制作《黄克诚》剧中,除了摄像,剧本的创作、编辑、剧组管理等等都不是他的本职工作,在拍摄工作中使用被告潇湘厂器材、人员等物质技术条件都是有偿的,何况潇湘厂也没有将原告制作《黄》剧的行为作为职务行为或完成单位任务来看待,因为陈1994年因忙于此事,没上缴款而被扣发工资。所以,《黄克诚》剧不是他的职务作品。两被告签订的协议规定的分配比例显失公平合理。 记者多次与潇湘厂联系采访事宜,该厂有关人员说:“最好不要报道。”在记者的坚持下,她说要找该厂的法律顾问,并将其手机号码告知记者。记者与法律顾问联系,对方却说要厂方授权才能接受采访。去年12月27日,记者再次与该人士和法律顾问联系,均无人接听电话。 4 判决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电视剧属于视听作品,创作过程复杂,需要众多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密切配合才能完成。在《黄》剧剧本的编写过程中,陈做了搜集史料等大量工作,但这仅与该剧的剧本著作权有关,并不涉及《黄》剧的著作权。 陈在筹拍和拍摄《黄》剧的过程中所做的大量工作,均是以潇湘厂电视剧部的名义实施的,因此该行为系职务行为。该剧的主要资金也是 A部门筹措或政府有关部门拨款构成的,潇湘厂负责拍摄,原告作为个人,不是《黄》剧的全部投资者,也没有委托潇湘厂拍片的委托行为或合作行为,不能取得《黄》剧的著作权。 法院还认为,我国对电影电视作品应当如何署名没有统一规定,从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来看,著作权所保护的是智力创作成果。作者对一部作品享有原始著作权,必须包含有独创性劳动成果。原告负责剧组管理等工作,不能认定为其个人具有创造性智力成果。潇湘厂和湖南 A部门约定联合拍摄《黄》剧,组织资金,并取得拍摄许可和进行拍摄,前者依法应享有《黄》剧的著作权,后者依据合同取得相关权利,两被告与中央电视台签订《黄》剧的转让协议,不构成对原告署名权和著作权的侵害。 依照2001年10月27日修改之前的《著作权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的规定,驳回原告对潇湘厂、湖南 A部门的诉讼请求。 1月7日,陈的代理律师朱妙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审判决以原告在筹拍和拍摄过程中的所有行为都是以潇湘厂电视剧部的名义进行的,从而认定原告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这是对著作权法职务作品、职务行为的一种曲解。 因为,《著作权法》第16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 根据2002年9月15日实施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工作任务”是指公民在该法人或者该组织中应当履行的职责。可见以谁的名义工作并不是判断标准,关键在于是否有“应当履行的职责”。 他还认为,一审法院以没有投入资金为由否定陈的权利,也是对著作权法的曲解。法律并未规定影视作品的制片者以投入资金为构成要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制片者必须解决和承担制片所产生的成本和经济风险,至于手段,则可根据具体市场环境加以选择,如拉广告、拉赞助等等。陈不是全部资金的投资者,但大部分资金是陈以及其他策划组成员筹集而来的,这一事实不容否定。如果以没有投入资金作为否定的理由,那么湖南 A部门和潇湘厂也不是所有资金的投入者。是否因为一方是单位,而另一方是个人,就可以“厚此”而“薄彼”呢? 他质疑说,一审判决以缺乏独创性智力劳动否定陈的权利,如果陈的大量工作不是独立的创造性劳动,那么原审判决提及的潇湘厂等被告成立拍摄组、组织资金等行为,有哪一项是“独创性智力劳动”? 他认为,随着制播分离,独立的制片人或制片人越来越多,他们对外开展业务经常是以单位的名义,但实际上风险自己承担,由此产生的利益之争会越来越多,亟待司法部门突破原有禁锢予以规范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