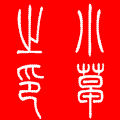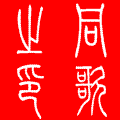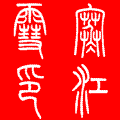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我们被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吵醒。仔细一看,原来是昨天从公社接我们下队的那些人。我连声说对不起表示歉意,赶忙坐起来穿衣服。
天啦,这哪里是我昨天穿过的衣服啊!一件八成新深兰色铁路制服和一件只穿了一个冬天的草绿色棉袄套在一起,被烧得从中间偏左起没有了右边,左边肩膀只和袖子有一点点布联着。一件卫生衣剩下下半身的一边还认得出是兰色,两条单裤留下长短不齐的四只裤脚,皮带象一段麻花,鞋子只有一只半。
陈本生的衣服也被烧了,虽比我稍微好一点,也好不到哪里去,留下的部分后来有女人给细毛毛改成两件毛毛衣,还看得出被火烧过。
那年头,谁会有两套冬服,这是我们的全部装备啊、、、、、、。
坐在床上抱着被子的我们,真的叫做下不得地。我望望屋里的人们,没有一个认得的,我多么希望有人在这个时候帮我一把,我会记得他一辈子。但是没有,连同情都没有。他们在议论一个中心话题,‘谁对这次起火负责’。认识统一以后,他们轮流向我们做表态式指责。具体说些什么写出来对读者无益,反正都是空话、废话,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我们一言不发的受了一肚子气。
等他们都讲完,我们还是只能抱着被子坐在床上,我问自己,怎么办?告诉家里?来不及。找谁帮忙?举目无亲。我试着问了一声:“昨天我们还有几个人住在哪里?”没想到这句话倒是提醒了他们,这时有人说:“把昨天来的知青喊来”『后来才知到,说话的这个人是队长徐跃云』于是他们分头去找人,这时天刚刚亮。
不一会儿,知青来了,『他们可能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大家都没做声,不知是谁提醒大家“谁带了搞劳动的衣服”这样大家先后散去,不一会儿一个个拿着自己的旧衣服又回来了。
陈本生命好,一是同班同学有五个,二是个子小什么都能穿,虽然旧一点可以穿得不冷。我可惨了,虽然个子不算大,但衣服都是小个子穿的,根本穿不进。找来找去,只有阎远兆有一件他故去的爸爸留下的旧棉列宁装能穿,但是好大。如果扣着穿,衣服里还可以钻进个小个子。他说:“这是我妈妈要我带来出工穿的,只是很旧了。”就是它了。穿着里衣套着大棉袄,左右一折,胸口有两层棉衣护着,再扎一根草绳,不冷。裤子怎么办,卞家老婆婆找了一条他去世多年的老头的扎头裤子给我,还短了一点。也不管它,系一根草绳扎住,不知谁送来一双可能也是已故之人留下的手工布鞋,可以穿,没有袜子。后来又看到一顶破棉帽,小一点,前面右边烧了一个洞,棉花露在外边,像别着一朵小白花。耳达子一边没带子系不起来,戴着它头上像张着高低不齐的一对小翅。动一动,小翅跟着上下翘。不管它,不冷就行。我只顾找穿的,不知自己打扮成了什么样子,这时有知青要我看看自己,我看着自己无奈的笑着说,“真像个土匪。”这样我总算可以出得去了。但是,洞庭湖冬天凛冽的寒风总是不断的提醒我下边光着身子,像没穿裤和鞋。
也因此我下乡第一天就给广阔天地的人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