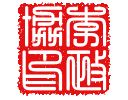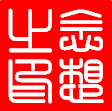忽然有一天,心血来潮想知道父辈年轻那段难忘的岁月,于是搜索到“知青论坛”。看各位前辈的回忆,不免也想起当年偶穿开裆裤的年代。
我记忆中的知青是什么样的呢?
三十年前,偶穿个开裆裤从前村跑到后村,对在生产队上的知青叔叔阿姨有些印象。你要想再问我前几年?咳,更小了,小鸡鸡除了尿裤子就是在地上拖灰……


偶记得的队上的知青有三个“妹子”——本来偶是该叫阿姨的,但偶奶奶他们叫得惯了,还是觉得这样亲切些。男的呢?本地人都叫“把子”,比如“外把子”、“红把子”可能说的是些“带把儿的”吧?若干年后偶和同辈一起出来打工,招聘市场那个招工的问:“你们俩都有什么特长?”,我那不争气的哥们不由自主地弯腰朝胯部望去——他呀,也只有那儿“特长”了,闹了我个大红脸。呵呵,扯远了不是?言归正传,说俺们生产队上那几个妹子。
三个妹子,一个姓胡,一个姓罗,一个姓周。好像周妹子是个鸭蛋脸,两个长辫子。罗妹子脸有些圆,白白净净的。偶捏,对那个罗妹子是又爱又怕。啵!谁敲偶爆栗子啊?偶那个年纪会好色吗?告诉大家吧,因为罗妹子擦雪花膏!好香!!!那可是绝对高级的东东。偶最多只擦三五分钱一盒的蚌壳油,哪能和雪花膏相比呀。罗妹子一见到偶就要一把捉将过来,往偶龟板似的小脸上涂雪花膏,疼得偶直想哭。所以呢,对罗妹子是又爱又怕,爱的是想闻她身上的雪花膏味儿,怕的是她给偶的小脸动手术。据说罗妹子本来不会游泳的,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罗妹子和几个知青社员坐船过渠江到太阳坪,快到岸船翻了,几番扑腾之后,罗妹子便无师自通地能游水了,真是奇才啊!几年后,生产队那两棵大杉树伐倒了,罗妹子淘到片刚锯下来的木板,高兴得如捡个大元宝似的。
男知青呢,记得两位:一个是赵志勇,另一个是黄千一。记忆中黄千一走到哪都挎一部收音机,在我们一帮小屁孩看起来简直是酷毙了。要说现在,大街上开部大奔也没当年一部收音机气派。想听收音机呀,你们先摔一跤,胜的才能听哦,于是,一帮小子开始了乱世三国里的打斗。当然,偶虽然小不能打架,但是很特别地经常能听收音机。黄千一回来晚了,食堂里没什么菜,就经常敲着个搪瓷碗到偶家问偶奶奶:“伯娘,还有菜吗?”于是偶奶奶就找出黄瓜四季豆什么的。有时候食堂里连饭也没有,总能在我家翻出块锅巴泡上菜汤将就一餐。所以偶经常能拿黄叔叔的收音机听哦。
回来再说说罗妹子,一见着她除了闻她的雪花膏香气,就是想问她要空的雪花膏盒子,那可是宝贝哦!小一点的盒子两头钉个孔,可以当口哨吹。大一点的可以养蚕,或者在冬天的时候,放块锅巴滴两滴油在火上烤吃起来可香了。
虽然雪花膏不能经常拿到,但对于我的确是个宝贝。当然,我们那帮小子,最好的宝物有好几件,第一是磁铁,这玩艺可神奇,能吸铁东西。谁要是有啊,一天到晚屁颠屁颠跟有人家后面指望他发善心让我玩两分钟。第二是弹簧,能长也能短。高枧渡口岸上经常有车抛锚,车修好开走后,我们一帮人冲上去,谁眼神好手快就能捡到弹簧什么的,最不济也能捡到个垫片。磁铁和弹簧偶是无缘的,偶太小,抢不到。一毛钱一个的陶制小鸡奶奶也不肯给偶买,想到这,偶不由得舌头根儿一酸——“啵”!各位叔叔阿姨,谁又敲偶爆栗子啊,偶招谁了?再敲,偶这头就成释迦牟尼啦。什么?不是舌头根一酸?我知道,那是鼻子根一酸。关键是这几天偶重感冒啊,两个鼻孔里塞满了鼻屎和浓鼻涕,一伤心,眼泪涌出来没下到鼻子里,那滴伤心泪好像台球王子丁俊晖打出的一记漂亮斯诺克,几个拐弯绕过鼻腔一转变到喉咙里了,于是,才有舌头根一酸嘛!打住,打住。谁扔的西瓜皮啊?嗯,还泼菜汤,里面有西红柿,味道不错……咳,板砖就算了啊,要出人命的。
话说因为想起当年偶奶奶没给偶买那陶做的小鸡哨儿而百感交集,舌头根儿一酸,掉眼泪了。但是,别看偶年纪小,其实还是很有自力更生的精神滴。每回渠江发大水,偶就跑河滩去淘宝。那时候生态好,下几天的雨也不过涨三五尺的水。河滩上往往能捡到电池的塑料盖、铜帽碳棒什么的,甚至能捡到玻璃球!那可就牛逼大了。能捡到的玻璃球一般是农用喷雾器的开关弹子,如果能捡到跳子棋,更是草鸡变凤凰了哦。有了里面红红绿绿的玻璃球,有磁铁的老大也得看偶的脸色了。
……未完待续。



















 期待后续。
期待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