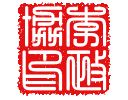哥哥姐姐们:
你们好!
我是“嫩”知青,白泥湖的知青是个挺大的群体,但是都是“嫩”的。今天也来哥哥姐姐们的茶座,发两篇短文先。不知有没有白泥湖的,看见了请顶一下!
苏 老 倌
苏老倌不姓苏,他姓陈,生于五十年代,大概其父母有感于苏联老大哥对中国革命的无私援助吧?在他的名字中有一个“苏”字。认识他时据说他母亲早已与他仍在服刑的父亲离了婚,并重组了新的家庭,还有了新的小弟弟。苏老倌的父母虽然都在世,但是在知青们的眼里他无异于一个“事实孤儿”。内向、敏感的性格让他默默承受着周围异样的眼光,在他十六、七岁的脸上,依稀过早地刻上了岁月的沧桑,大家都叫他苏老倌,没有人觉得不妥。这个瘦瘦高高的知青,其实蛮有才,花鸟虫鱼随手画来活灵活现。不过这个绘画的爱好也曾给他惹来不大不小的麻烦。记得当时我在知青连掌管着一个“小卖部”,其实就是代销一点肥皂、牙膏、信纸、邮票等知青的必需品,还兼管着邮件的收发,印象中就没有过苏老倌的信件。一天,苏老倌走进会计室(“小卖部”就在会计室里),要买四分钱的邮票,我告诉他,四分钱邮票只能寄到湘阴,寄到长沙的信要八分钱,他悻悻地走了,过了一天他凑齐了八分钱又来了。买了一张邮票,贴上信封后他没走,坐在会计室与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一会。(他听说我父亲在文革中被逼死了,大概同病相怜吧,和我能聊几句)这其间,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在信封上画了起来,有花卉、有蝴蝶、等等,等等,信封的四周和背面都画满了。我当时只觉得刹是好看。不料想几天后,这封信被退了回来,原因是“信封上不得乱涂乱画!” 唉!可惜了那八分钱的邮票!
七四年的夏天,一个惊人的消息在知青连队传开了:苏老倌失踪了!经调查,最后一个看见他的人证实,他是一个人拿了一条毛巾走出连队的。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连队得到通知:在湘江涨水淹没的芦苇荡里漂起了一具死尸,快去认尸。带队干部领了七八个男知青心慌慌地赶到湘江边,费尽周折总算把死尸捞上了岸,尸体早已腐烂,臭气熏人,手电光下实在无法辩认,经商议决定留下死尸,知青们先回连队,待天亮再作处理。全连队的人虽然没有等到确切的结论,却莫名地蔓延开了一种恐惧。原本与苏老倌同一寝室的几个室友,死活不敢回房睡觉,更有那恶作剧的男生,半夜躲在上厕所的必经之道处,装神弄鬼,战战兢兢地喊“苏老倌来哒…,鬼来哒…”。几个麻起胆子上厕所的女生,被一扑面而来的黑影吓得跌坐在地,哇哇大哭。我正在暗自为苏老倌的不幸身世伤感,听到外面的哭叫声,跑去一看,那“黑影”原来是一个稻草人,外面套上了苏老倌的衣服。我不懂这些同学怎么这样冷酷,苏老倌死了你们就不心痛吗?忍不住将稻草人狠狠地扔出去,喊道“苏老倌又没死,他不会死的!” 第二天,校部正式通知我们连队:那死尸不是知青,是一当地农民。
过了些日子,一个大白天,连队又传来了“苏老倌来哒”,“苏老倌来哒”的叫声。是哪个又在装鬼?循声望去,没错,是苏老倌!是失踪多日的苏老倌!明晃晃的阳光下,他面带笑容,手里拎了个线网袋,里面装了个脸盆,还有几本《十万个为什么》。他高兴地告诉大家他去看他爸爸去了,他手里的东西都是爸爸送给他的。
几个月后,长沙市民政局有少量的名额来招工,条件是照顾特殊困难的知青就业,不知是苏老倌的不幸身世令人同情,还是害怕他再出意外,给了一个名额给他。分配在长沙市二十九中,当厨房里烧火的普工。连队的知青并没有忘记他,有回长沙的就会去看望他,但是带回来的消息却越来越让人揪心:苏老倌离开知青连时就不太正常,回长沙后越来越神经,后来听说他已不能正常工作、正常生活,常常不吃不睡,一个人坐在高高的树杈上发呆。在大部分知青陆陆续续回城的时候,传来消息:苏老倌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