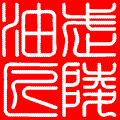周小春,好学生,门门功课打百分。
长大了,当先生,拿起个教鞭打学生。
——童谣
因为一点福利上的小好事,我匆匆的往财务处赶,没注意一个人迎面而来又擦肩而过。“哎!陈老师!”从后面传来又惊又喜的声音,我一回身,这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便笑呵呵的站在我面前了 。“陈老师!”比我高出一个头的小伙子又喊了我一声。“楚军?你是楚军!”“是,是的。陈老师好?我是楚军呢。”我拉过他的手,拍了拍他的肘胳膊,完全是成熟男子的铁一样的臂膀了。我笑问“楚军,小时侯的事,还记得么?”“记得,怎么不记得?”“是这条胳膊么?”“那就记不清了”小伙子有点腼腆起来,“陈老师还记得,其实真的一点也不痛呢!”“还是这句话?”我开心的笑出声来,楚军也跟着我笑,几十年前的那一幕出奇相似的重现了。
应该是二十五六年前,我教小学二年纪的算术。学校给每人配了一只多用笔,其实作笔用只有一种效用就是圆珠笔,但笔身是四节不锈钢管迭套起来的,一节节抽出来有尺多长,就是一根理想的教鞭。我在自己的手板上敲了敲,发出的“啪啪”声挺响,却不感到怎么痛。我收起来放在兜里心想这玩意真好!
我上课总是把它抽出来捏在手上,有时用它来指点黑板上的演算题,但多数是在讲台上敲打,它发出的“啪啪”声最能让学生一下就安静下来。我最喜欢的是学生看书或做作业时我一边用它轻敲着我的手掌,一边来来回回的看学生,遇到做别的事的,或者把头埋在桌下玩东西的,就敲敲桌面或者书上,一句话都不要说,教室里安安静静的。
这天的第一节课就是我的,教“除数和被除数的认识”,因为内容有些多,所以留出的课堂作业时间较少,学生们有些听疲乏了的意思,有几个还呆呆的坐着不动笔。我感觉今天的课肯定上成“夹生饭”了,心里便有些焦躁起来。这时一个伏在桌上的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了过去。
这学生靠左边外窗坐着,他的头枕着弯曲的左臂伏在桌上,脸朝着窗外,右臂随意的搭在桌上。并未意识到我到了他身边,只顾看着后山树枝上跳跃的的小鸟儿。我在他的两臂之间的桌子上使劲的敲了两下,头一下的“啪”声其实就已经震醒了他,但带着我的震怒惯性的第二下又落了下去,而且第二下恐怕比第一下更重,但发出的“啪”有些异样了,因为这一下没落在桌子上,不偏不倚的落在孩子抬起身前顺势收拢来的小臂上!马上,从肘弯到手腕这一节的胳膊上一条红肿的击痕出现了,孩子一下坐得笔直的,迅速收起这条胳膊,眼睛却不敢望我。
教鞭从我的手里滑落到地上,我顾不上它了。我掰开孩子紧搂着的臂膀,托起这条被我打伤的小小的手臂察看起来,已有些红中带紫了。教室里安静极了,一双双惊恐的眼睛看得我心里发空,但我暂时还顾不上这个。我说:“同学们,老师闯大祸了,大家自己做作业好么?我带楚军到医务室去。”我一边朝伤痕吹着气,一边问:“好疼吧?楚军。”这个不怎么爱说话,还不怎么习惯同老师说话的小男孩子这下倒来安慰我了:“老师,你莫急咧!一点都不痛!”接着又补充说:“还有点痒咧!”我当时还没做母亲,但孩子的这句话还是使我有一种冲动,我摸了摸他的头说:“老师对不起你,走,咱们去医务室。”
校医见了后说没破皮不好搽药,就只涂了些活血的红花油,这一来,小小的胳膊又红又紫又亮,真的蛮吓人了。我愈发的急起来,问楚军:“我送你回去好啵?上不得课了吧?”“不咧!”他看了看胳膊,说:“我不要搽这些药,真的一点都不痛。”上课铃响起了,小家伙把袖子放下撒腿就往教室跑了。
整个上午我都想着这事,后悔得要死。我到校长那里自首了这件事,校长自然批评了我,让我自己解决。我一下课就跑到教室里看那个胳膊,也就听了好几次楚军对我说的“一点都不痛了”。第四节课下课还差五分钟时,我就来到教室外等候,然后和他一起去他的家见他父母。
路上,楚军一直在说我不必送他回家,他的胳膊好了,还说只要他不挽起袖子,爸爸妈妈都不会晓得他挨了打,他真的一点都不痛了。我突然明白了:他是怕我借机去他家“家访”,告诉他爸妈他上课开小差,到现在为止,他都没认为老师做错了,只是记着自己为什么挨了打——因为没做课堂作业,因为山上树枝上跳跃的小鸟。我感动起来,因为一个小孩子对老师无条件的宽容,因为一个小孩子没有打算记恨老师的干净的心灵,而在我,早就忘了我为什么而打了他,只是记住了那赫然的红紫的伤痕!我又摸摸他的头,对他说:“楚军没错,山上的小鸟也没错,老师嘛?错了一点。主要是老师向妈妈认个错,没楚军什么事。还有,老师请妈妈帮忙给楚军涂药呢。”小家伙才没坚持了。
到了家门口,我有点心虚起来,让他走前面。就在这时,他的父母同时看到我,都非常热情的招呼我进门。“老师请坐,是不是楚军闯什么祸了?”他妈妈一边泡茶,一边带着歉意向我询问,而做爸爸的则已经把责备的眼光朝向了儿子。“不是、不是,不是他的错,他没错。”我慌忙站起来,一边抚慰似的摸摸孩子的头,因为他已经有些害怕的神情了。
“楚师傅,我今天不小心”我一边斟酌一边慢慢的说“用教鞭敲桌子的时候,打伤了楚军的胳膊。”“冒伤咧!”我的学生马上插嘴“一点点红,一点都不痛。”做妈妈的紧张起来,做父亲的却沉得住气,还是问了句:“冒脱噻?”“那倒冒,但也蛮吓人,你们看了莫紧张。”我让孩子挽起衣袖。不知是涂了一上午的红花油发生了药效,还是我和楚军共同的心愿起了作用,抑或是孩子超乎寻常的康复机能,那伤痕竟不是上午那般的骇人,红紫还在,但面积小些了,而且不油亮了。
做妈妈的舒了一口气,作爸爸的也不易察觉的缓和了脸上的表情,但马上又敛色对儿子说:“你肯定调皮捣蛋了,不然老师不会敲你的桌子。”“没有、没有,他没有调皮”我眼睛看着楚军,“他只是有点打瞌睡,怕是昨晚睡迟了?”我眨眨眼,意思是:我当老师的,不能撒谎啵?“是,是的,昨晚睡得迟,走人家好晏才回”做妈妈的赶快出来打圆场。我又赶紧作检讨,还说上午校长已经批评我了,下次再不敢带教鞭进教室。“陈老师莫紧张咧,细伢子不打不成材”楚师傅一边喊我喝茶,一边说“细伢子打大的,我们小时侯,爷娘不做人打咧,现在哪个恨爷娘罗?”又回头教诲儿子:“你看你,害老师被校长批评。”“不、不怪他,是我不好”我一边继续认错,一边起身告辞,一边嘱咐楚军小心伤处,楚军笑着说:“真的一点都不痛了,还有点痒呢!”我在楚师傅夫妇热情留我吃饭的张罗声中出了他家的门,才真正放下心来,楚军一直把我送到楼梯口才硬被我喊回去了。
从此,我再没用过教鞭。
眼下,看着高出我一个头的楚军站在我面前,看着他已经成熟但依然诚恳的笑容,我仍然有一种摸摸他的头的渴望,但肯定摸不到了。不过我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