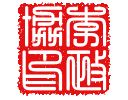我们开荒挖出很多树蔸子,树蔸子经得烧,是很好的柴火。五月一个艳阳天,我把一大堆树蔸子摊开摆了一院子,想晒干留起来以后好烧。F君走进屋笑着对我说:“你有味啵,晒树蔸子把路都堵死哒,还要人家走路吧?”
“就是要拦路,何解噻?”
“你(把事)拦我吧?”
“嗯啰,就是要拦你,你要何解?”
F君顿时表情严肃的看着我,沉默良久,对我说出了我这辈子只听到过一次的三个字,并认真地问我知不知道他长久以来对我的心意,我点头。他又问我“可以吗?”我摇头。他说:“莫摇头,你考虑考虑。”我听完目无表情的离开了。别看我表面平静,从容地点头、摇头,从容离开,其实我吓坏了,话都说不出来。我简直就是落荒而逃,一连三天没去园艺场。
F君来到我的住处找我,问我是否生病了。我把一张写了两句话的小纸条塞在他手里,“另找知心人,相爱到永远”。我心乱如麻,总觉得想哭,觉得无法面对。自己年纪小,从未考虑过交男朋友,那个年代的观念,谈恋爱事关终身,F君调皮出名,张扬的个性,要过长辈那一关绝无可能,我只跟家里人试探了一下,就被骂得狗血淋头,岂敢做出大逆不道之事。再者,虽然心里喜欢,虽然平生第一次受到这样强烈的感情冲击,但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爱情,不敢轻率。
接过纸条,F君递给我一个厚厚的本子,打开一看是本日记。日记里记满了我们相处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浸透了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慕与热情。我被这本日记感动,我被这本日记打动,寻思自己怎么能给他那样一个答复呢?可抬头发现F君早已不在面前,我好像伤到了他。
回到园艺场我们没有了话讲,也不唱歌,空气似乎凝固了。
一场端阳雨下得不能出工,F君说:“出去走走”。于是高挽裤脚,两人共一把雨伞,在公路上向县城方向走去。雨中我们有了第一次关于感情的对话,也成了决定命运的一次长谈。谈话间,我心里直打鼓,暗想他要是再提出来,我就逃不掉了,我会答应他。或许是出于自尊、或许他真是怕我为难,他并没有再提,而是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绅士一般地告诉我,喜欢你另有其人,他可能更适合你。最后他说:“我永远会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我回到家一个人关起门痛哭了一场,不知是为自己还是为他。
F君没有食言,此后我俩依然友好如初。离开园艺场各自回生产队以后,虽然不再有那种田园乌托邦似的美好生活,我们还是常有来往,他过生日接我去他那里吃饭,我生病他会来看我,也经常一同去找我们共同的朋友玩。有天他带朋友来玩,我杀鸡给他们吃,他回去后写了首打油诗,什么“今日补鸡一只,夜不能寐,云云……”惹得大家开怀大笑。
F君每次回家探亲,我们都有书信往来,记得有封信他告诉我正在看《红楼梦》,并常与父亲探讨,我回答他“你父亲学问高深,何不与他好好探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现在想来真是幼稚可笑。(我后悔没把日记和书信保存下来,纯真年代的感情应该尊重,值得珍藏。)
回老家探亲我曾顺道到F君家小住,开明的父母非常理解我们的友情。温厚慈祥的母亲,深夜还在与我细谈多年对孩子的深情与牵挂;幽默健谈、爱好书法的父亲,亲笔提字送给我,勉励我们在农村要努力上进;与我同岁的妹妹一见面即相互视对方为知己,通了很长时间的书信。他们让我与F君相处更象家人。
离开靖县是F君亲手帮我打包行李,一直把我送上汽车。分手时,我们并没有什么道别的话,也没有任何承诺与期待。(待续)
“就是要拦路,何解噻?”
“你(把事)拦我吧?”
“嗯啰,就是要拦你,你要何解?”
F君顿时表情严肃的看着我,沉默良久,对我说出了我这辈子只听到过一次的三个字,并认真地问我知不知道他长久以来对我的心意,我点头。他又问我“可以吗?”我摇头。他说:“莫摇头,你考虑考虑。”我听完目无表情的离开了。别看我表面平静,从容地点头、摇头,从容离开,其实我吓坏了,话都说不出来。我简直就是落荒而逃,一连三天没去园艺场。
F君来到我的住处找我,问我是否生病了。我把一张写了两句话的小纸条塞在他手里,“另找知心人,相爱到永远”。我心乱如麻,总觉得想哭,觉得无法面对。自己年纪小,从未考虑过交男朋友,那个年代的观念,谈恋爱事关终身,F君调皮出名,张扬的个性,要过长辈那一关绝无可能,我只跟家里人试探了一下,就被骂得狗血淋头,岂敢做出大逆不道之事。再者,虽然心里喜欢,虽然平生第一次受到这样强烈的感情冲击,但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爱情,不敢轻率。
接过纸条,F君递给我一个厚厚的本子,打开一看是本日记。日记里记满了我们相处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浸透了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慕与热情。我被这本日记感动,我被这本日记打动,寻思自己怎么能给他那样一个答复呢?可抬头发现F君早已不在面前,我好像伤到了他。
回到园艺场我们没有了话讲,也不唱歌,空气似乎凝固了。
一场端阳雨下得不能出工,F君说:“出去走走”。于是高挽裤脚,两人共一把雨伞,在公路上向县城方向走去。雨中我们有了第一次关于感情的对话,也成了决定命运的一次长谈。谈话间,我心里直打鼓,暗想他要是再提出来,我就逃不掉了,我会答应他。或许是出于自尊、或许他真是怕我为难,他并没有再提,而是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绅士一般地告诉我,喜欢你另有其人,他可能更适合你。最后他说:“我永远会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我回到家一个人关起门痛哭了一场,不知是为自己还是为他。
F君没有食言,此后我俩依然友好如初。离开园艺场各自回生产队以后,虽然不再有那种田园乌托邦似的美好生活,我们还是常有来往,他过生日接我去他那里吃饭,我生病他会来看我,也经常一同去找我们共同的朋友玩。有天他带朋友来玩,我杀鸡给他们吃,他回去后写了首打油诗,什么“今日补鸡一只,夜不能寐,云云……”惹得大家开怀大笑。
F君每次回家探亲,我们都有书信往来,记得有封信他告诉我正在看《红楼梦》,并常与父亲探讨,我回答他“你父亲学问高深,何不与他好好探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现在想来真是幼稚可笑。(我后悔没把日记和书信保存下来,纯真年代的感情应该尊重,值得珍藏。)
回老家探亲我曾顺道到F君家小住,开明的父母非常理解我们的友情。温厚慈祥的母亲,深夜还在与我细谈多年对孩子的深情与牵挂;幽默健谈、爱好书法的父亲,亲笔提字送给我,勉励我们在农村要努力上进;与我同岁的妹妹一见面即相互视对方为知己,通了很长时间的书信。他们让我与F君相处更象家人。
离开靖县是F君亲手帮我打包行李,一直把我送上汽车。分手时,我们并没有什么道别的话,也没有任何承诺与期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