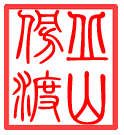我和父亲对大姐的愧疚
大姐是我们家遭遇灾难时的顶梁柱
我的大姐今年已经60岁了。43年前,漂亮、心高气傲的大姐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读高中,也不能去话剧团当演员,下放到湖南的江永县当知识青年。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湖南日报社的经武路宿舍,这里是湖南日报社的老办公楼,典型的苏式建筑,中间一条又长又窄的走道,左右两边的房子门对着门,住的主要是原湖南日报右派和我母亲单位的职工和家属,我家住南边最后那间。
1968年春天,我的父母亲双双失去了人身自由,除了扣发他们的工资,还不准他们回家。
俗话说,祸不单行。这年3月的一天,湖南日报造反派“红色新闻兵”在我们院子的围墙上贴出一张“勒令”,勒令我家在几天内滚蛋!那时候,被关押在兴汉门新华印刷一厂的父亲束手无策,母亲则远在丁子湾的学校没有任何消息。3月19日,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上午,在我们给父亲送衣物时,“红色新闻兵”来人踢开我家的门,生生地把我家(除了借用公家的床铺、椅子外)的东西统统扔到走廊上,把门贴上封条后扬长而去了!我们姐妹在走廊上趴着、蹲着度过了几天后,我的大姐,20岁出头的大姐,从江永回来了!大姐先把我(13岁)和三姐(15岁)安顿到也是知青的男朋友家中,然后把书柜书桌等家具分别寄放到其他知青同学家。离开经武路宿舍的那天夜里,我从窗户爬进房里,在地板上拉了一堆大便,算是对被“赶走”的愤怒和抗议的表示吧。
接下来,大姐带着我和三姐东奔西跑,张罗着找房子。5月间,大姐初中同学的哥哥介绍了两间住房,每间9平方米,外加厨房和堂屋(与人共享),爸爸用家里最后的150元存款付了首期,(未付的100元一直到1978年父亲平反后补发了工资才得以付清)。在大姐同学的帮助下,我们搬进了长岭29号。就这样,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大姐就是家长,担起了父母的职责,是家里的顶梁柱。
大姐和知青被“遣送回农村”
这以后,我们三姐妹过了一段愉快的生活。我记得,那一两年里,父母能每月回来一次了,家里总是有很多哥哥姐姐,都是大姐的江永县知青。我不知道在乡下大姐得了关节炎,两只膝盖都红肿了,根本不能下水田。乡下知青大都已经生活不下去了,他们绝大部分都回了长沙。知青们回来后,靠着家里一点微薄的口粮,偶尔打点零工,挑土什么的度日子,知青之间相互接济为生。
大概是1970年秋天,城市里掀起了赶知青回农村的运动。没有户口的知青叫做“倒流城市”,运动的主要方式是半夜突然上门“查户口”,好几次半夜里我们三姐妹被“查户口”的敲门声惊醒,我和三姐躲在被子里听着大姐去开门,听着大姐喃喃地说着一些什么“家里冒(没有)大人”、“乡里冒饭吃”的话,听着“查户口”的人的吼叫声和呵斥声。这期间大姐还到同学家里躲过几天。没多久的一天夜里,“查户口”的人又来了,我和三姐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眼睁睁地看着大姐被来的人连拽带推地弄走了。第二天一早,听对面的王阿姨说大姐被关在街道派出所。我和三姐连忙去找她。
我们来到左家塘街道办事处,一进大门,上班的人还没到,厅屋里黑咕隆咚的,这时一阵哭喊声传来,是大姐的哭声!她在叫“五毛!六毛!”(三姐和我的乳名),我们循声找去,里面还有一间内房,大姐是从窗户里看见我们进去的。内房大概是临时用来作“牢房”的,门就是用几根木棍钉起来的“牢门”,我们很害怕,离“牢门”远远地跟大姐见了面。大姐抓着“牢门”的木棍,哭着说,“赶紧去找爸爸妈妈!把我救出来!”还说:“要是回江永我会饿死的!”我和三姐害怕地小声地抽泣起来。这时候,门外进来了一个女的告诉我们,说要把大姐和其他抓来的知青“遣送回去”,要我们在两天内给大姐送些衣服,送点钱去……
大姐落难时父亲和我行了不义之举
接下来的事使我难以忘怀,更难以启齿,因为涉及我的父亲,一位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其实,我们六兄妹中,父亲最疼爱的是大姐。大姐在父亲人生巅峰的时候出生,父亲视她为吉祥,大姐的模样脾气个性也最像父亲。可是,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由于长期的运动,加上迫害和压抑,父亲的心理变得扭曲、性情暴躁。父亲虽然肯定大姐在危难之际拯救了家庭,却不能忍受大姐和知青同学相互来往,家里变迁时丢失了一些书籍,如《鲁迅全集》等,父亲老是拿来说事,一说就大发雷霆,怪大姐的同学“偷”走了云云。父亲对大姐的男朋友也不满意。父亲对大姐的态度,给我和三姐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也一度认为大姐和知青同学不回农村是“在城市吃闲饭”,是“好吃懒做”。大姐的知青同学要我学画画,借世界名著给我看(如《简爱》、《斯巴达克斯》),我也以为那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搞不清父亲和大姐谁对谁错,甚至以为家里的不安是大姐“滞留城市”造成的。
对于“遣送知青”的行动,父亲采取的态度很坚决。我记得的情节是这样的:回家发过脾气后的父亲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从此与***(大姐的名字)断绝家庭和父女关系!”要我们送到办事处,去“表明态度”。当时三姐就不肯去,我呢,懵懵懂懂地犹豫着:去吧,真觉得这是一件做不出来的事情,大姐不是要爸爸救她么?爸爸怎么能在这种时候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呢?不去吧,一来没有不听话的胆量,二来也认为大姐真的是犯了什么错,要不然,大人怎么都这么说,这么干呢?我拿了几件衣服,匆匆地走到办事处,我不敢去见大姐,把衣服和纸条往那个女看守一塞,像贼一样赶紧地跑了。我当时的感觉是这辈子见不到大姐了,自己没脸见她了。
没曾想到,过了几天,大姐又回来了!她兴奋地告诉我们,办事处把她和一些知青集中起来弄走后,汽车开到零陵时抛了锚,他们几个知青同学趁押队的不注意就跑了,没钱坐车,走了三四天,还讨了饭,才回到家的。这时候,我似乎觉得大姐好像并没有收到我送去的衣服,可是我又不敢问她,她也没有提起这事。
我代表父亲向大姐表示心中的愧疚
37年过去了,父亲、大姐、我和三姐,谁也没有提起过送衣服和纸条的事。我们都想借时间的流失抚平心头的伤痛。父亲在平反后几次说到大姐是我们家的功臣,要把长岭房子三分之一的份额给大姐。我知道,父亲这是想还账,还当年欠下大女儿的感情账。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12年了,可是我的心病越来越重。我经常想起大姐被抓走“遣送回去”的夜晚,大姐那“五毛!六毛!救我!”的哭喊声时常在耳边想起。
在这里,我,还代表爸爸,为我们当年无知、冷酷、愚蠢的举动追悔莫及,请大姐接受我和爸爸的忏悔,愿来世我们还是父女,还是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