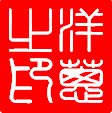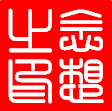我的情郎(一)
——写给逝去的青春岁月、
写给有着美好感情记忆的朋友们
《我的情郎》是一首歌:
我的情郎出征时路过的地方,
看那原野一片金黄。
如今啊,
成熟的五谷,
黄金般的波浪一样;
晚风啊,
吹得是多么的欢畅,
把这丰收的喜讯传扬。
朝露正凉,
月光还亮,
田野里赶牛忙,
胸前的热汗湿衣裳,
不由我思想起在战斗中的情郎。
这首文革前的电影歌曲是F君教我的。说到情郎,人们一定会把他界定为有男女之情或暧昧之意的人,不会把只有友情的人称为情郎,而友情与爱情之间的情感该怎么界定,很难说清楚。我与F君之间应该是有着这样一份情的。
初到靖县插队,我们都还年少,F君十九,我十七。修312公路时第一次照过面,没打过交道。听说他蛮调皮没大注意。公社办园艺场我们分别被所在生产队派去,从此便有了故事。
F君调皮是名不虚传。园艺场有个村姑叫秀秀,特别害羞,一看到男的就脸红,尤其看到F君他们这些大胆看女孩子、大胆跟女孩子搭讪的男知青,惟恐避之不及。秀秀越这样,F君越是要捉弄她。每逢休息,秀秀坐哪里F君就坐得哪里,跟她挤一条板凳。秀秀往旁边让一点,他就靠近一点,秀秀边让边骂,他边挤边笑,秀秀欲起身,被F君一把攥住:“你怕什么啰,我又不吃人”,秀秀气得叫:“娘哎,挨刀的呀,你像个棉被的个,越打越泡(抛)啊”。后来秀秀老让我坐他们中间,希望我帮她抵挡F君的骚扰。
F君在我面前倒是规矩起来,全然没有了过分的举动。
那是春末夏初的夜晚,习习晚风中,我们园艺场总是响彻歌声。女社员天黑就聚在煤油灯下衲鞋底,男社员抽袋烟就睡觉,只有我们几个知青就着月光聊天、唱歌,《我的情郎》就是那时候跟F君学的。跟他学了不少歌。有位知青有本外国民歌200首,那时我们几乎把里面的歌唱了个遍。
“恒河与加木纳河哟,多么的深广,我左思右想无可奈何,只得渡河走……”
“当月亮倒映在那湖上,垂柳随晚风飘扬,沿着弯曲的小路,送你直到月西沉……”
“在贝加尔湖旁的小屋,环绕着紫色的薄雾,我不寻找着这小屋,但绕过她也不易……”
“茫茫大草原,路途更遥远,有个马车夫……”
……这些歌或凄美、或忧伤、或轻松、或愉快,我们的情绪随着歌中的情绪变化、起伏,年青的心也被自己的歌感动着、吸引着。
那一段,我们手头有不少好书,经常交换着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双城记》,还有《苦难的历程》、《红与黑》、《红字》、《斯巴达克斯》、《玛丽·白登》,契可夫、普希金的短篇集……不计其数。交流读书的感受非常惬意,我们有着共同的书、有着共同的歌、更有了共同的话题。那是我在农村生活得很充实的一段时光。
F君和我有着极为相似的家庭背景,一接触就有亲近感。F君风趣幽默,谈笑风生,有他的场合,总是热闹又开心,加上都爱看书、爱唱歌,更有了黏在一起的理由。说实话,那时候年纪小,跟他在一起好象完全没有性别意识,在一起就像跟家人一样自然。我跟他无论上山砍树、下地种菜、还是收工歇息都是讲不停、唱不停、笑不停,。F君记性好,歌词都记得,一些别人不大唱的歌,像《江姐》里别人不太唱的华为等的唱段,他都记得。“牧童之歌”、“苏珊娜”、电影《十字街头》里“春天里百花香……”等等快乐的歌,被他一字不落的来回唱,他虽然唱得不算好,但总能以愉快的情绪感染别人。让人感到那时艰苦的生活环境因为有他而改变了颜色。我原本不是个放得开的人,跟他在一起变得开朗,我们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
我煮饭,他打趣道:“好点煮呵,莫把抹布跌得锅里一路煮把我们吃呵。”
“就是要煮抹布!”
我洗衣服,他讲:“你别个的不洗只帮我一个人洗吧。”
“那是的,好过!”
他有段时间离开了园艺场,另一位知青对他说:“你不去,人家歌都不唱哒”。他回来后对我讲“你是离开男人过不得日子啵?”
“你神经咧!”
有天我洗衣服,他随我一同到井边,蹲在旁边看我洗。天热,我脸上流汗,他突然抬手替我擦,这一刻我看到了异样的眼神,心里一惊,连忙回避。若不是有晚霞作障,脸红心跳的样子倍感难堪。(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