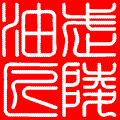9月24日,阴 小雨
清晨,梦中感到一点凉意,赶紧盖上被子。听到窗外有淅淅沥沥的小雨声,迷迷糊糊想,靖县人民真有福气,昨天的县庆活动有天帮忙,阳光普照,要碰上今天这样的天气,还不把参加活动的小朋友给冻感冒了。又躺了一会,突然惊醒了,“今天要去甘棠龙峰八队呀”。我连忙爬起来做准备。
靖县的领导对参加县庆活动的人特别关心,今天还为即将离开靖县的人准备了丰盛的早餐。我们一行准备到甘棠去的人都到了鸿运宾馆。我这人有点植物神经紊乱,想起今天要到久别了的生产队与35年没有见面的乡亲们见面,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了,就盼着甘棠镇的汽车早点来。
县庆组委会的人知道呵呵、富裕中农和我们几个老知青要到甘棠去,专门通知了甘棠镇的领导,镇里特地来了一辆伊维柯,还由镇人大主席,纪委书记专门陪着到村里去。
汽车一离开县城,我的心就像车子一样飞驶起来,随着艮山口,响水坝这些熟悉的地名牌一一闪过,很快就到了太阳坪“高靖港”(当年队上人就这样称呼这条河,我也没弄清是哪几个字) 。
1969年元月下乡时是先下了汽车,然后登上那靠人力攀拉钢索的船过的河,后来72年回长沙时又是坐同样的船与送行的乡亲们告别。今天过河不用下车,直接就可以坐着车过河,但谁也没有想要过一把这方便快捷的瘾。不知是大家想在桥上再看看这条“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的界河,还是有意再重温一下当年下车登船的感觉,到了桥中间一致喊“停,停,停”。
车刚停,大家就拉开车门下车,跑到桥边手抚桥栏极目远瞰。天还是那天,水还是那水,这走近甘棠的第一个熟悉的地方,让大家几乎挪不动脚步。转过来,看过去,走几步,照相,又走几步,再照相。刚好远处的铁路桥上一列火车经过,隆隆声中,我百感交集。当年这条小河可说是甘棠谋求发展和与外界联系的天堑,而今变成了通途,汽车、火车都畅通无阻。我顺着伊维柯汽车司机的手看去,透过那层层的树林,就是我们当年登船上岸的渡口。看一眼那几乎分辨不出来的渡口,看一眼脚下宽阔的大桥,再望一眼不远处的铁路长虹。。。。。。我敢肯定,任你怎样的好手,也描绘不出此时的心情。
车子驶进甘棠镇政府后,镇领导要我们先休息一下,他们要安排人带我们到各村去。已经到了日思夜想的甘棠,谁还能安心坐着。大家都说先去看甘棠坳老街,镇领导非常理解我们,专门由一位领导陪同。
大家几乎是小跑着爬上一个坡,上坡后,一眼就看到了当年甘棠公社的老粮站,这个几乎每个甘棠知青都难忘的地方。这里,就是知青们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知青们就在这儿接受最后的安置,跟前来接人的贫下中农去将要扎根的地方。
眼前的粮站静悄悄的,院子里堆了一些烟叶什么的。但此时我的头脑里,却立时出现了当年刚到达时的热闹场面:那么多人来接人,有各队的社员,也有早个把月下乡的知青,整个粮站包括外面坪里闹嚷嚷尽是人。。。。。。一时又闪出我们费尽力气挑担谷子来交公粮,却因保管员说谷子不够干,不得不又在这粮站的坪里摊开晾晒的场景。石头与砖混砌的围墙,几十米长的大院子,白墙黑瓦的仓库,几乎原封未动,可再也没有人来交公粮,再也没有前来交粮的知青。
我们一行沿着老甘棠坳边走边看边讨论,这儿是原来的××,那儿应该是原来的×××。
我离开甘棠坳35年了,什么东西经过35年都会有变化。当年的甘棠坳是整个公社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不用说在赶场的日子整个坳水泄不通,就是平日也是人来人往,喧闹不停。也许镇政府迁出了原址是主要原因吧,如今的甘棠坳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一栋栋老的木板房子更加破旧,整个坳,或者称其为街道,都透着一股衰败和凋零。安静的甘棠坳突然来了这么几个手执照相机,东张西望,不停照相的人,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些老住户很快也就知道这是来了一伙当年下放的知青。
当我们来到当年知青最喜欢光顾的地方,那个能决定改变知青命运的公社革委会时,我们身边已陆续跟了一些人。这个当年最有权威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养老院,房屋依旧,后院墙上的标语依旧,那一幅依稀可辨,应该是ZZJ写的仿毛泽东诗词的对联也依旧。不同的是,当年公社领导办公的地方,现在却住着几十个年老体衰,没有亲人依靠,全凭政府救济养老的人。
就在我们里里外外,楼上楼下地寻觅旧时印象时,跟着我们走的一位当地老人主动上前说,这个养老院里住着一位可怜的长沙下放知青。一听说有长沙下放知青在这个养老院里,让我们大吃一惊。大家一齐拥到养老院的住院人员一览表前,在那位当地老人的指点下找到了“杨顺崇”这个名字和他的照片。富裕中农,呵呵和念想把照片拍下来后,急切地问这个杨顺崇在哪里,我们要见这个人。但养老院的人说杨顺崇出去了,到哪儿去了也没个准。围观的也有人说,这个杨顺崇不是长沙知青,呵呵则坚定地说:只要是知青,不管是哪里的,我们也要看到他。我们请他们帮忙去找找,找到了告诉我们。
就在我们出了养老院没几步,围着的人说“来了,来了。”我顺着人群闪开的道望去,远处走来一个穿黄军装的人。他那身打扮和表情,让我们一惊,这人神经了。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想从他嘴里多了解一点他的真实情况。终于,在呵呵耐心和反复的询问下,这人说出了他的名字,讲他是从哪儿下放的,下放在哪儿,与他在一起的有哪几个人。呵呵凝重地说:他讲得没错,他是个知青,他讲的那几个人我认识。
我看着眼前这个穿着一身不知道是哪一年制式的军装,身背棍子当刀枪,穿着一双长统套鞋,脸上笑嘻嘻的步入老年的人,心里一阵酸楚,怎么也无法把他和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知识青年联系起来。但30多年的岁月,苦难的经历,硬是把一个活生生的知青,变成了这样一个思维还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初,没有了生活自理能力,注定要在这养老院里度余生的已经疯了的苦命人。
我们心里都很难受,富裕中农掏出100元钱就要递给他,我犹豫了一下说,把钱交给他?富裕中农回头很无奈地说:也只能这样了。是的,把钱交给这样一个已无法保护自己的人,余下的结果只有天知道,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四名甘棠的老知青由富裕中农作代表,把400元钱交到杨顺崇手上,嘱咐他好好生活。围观的人群看到这一幕,有的说,这杨癫子这次还晓得要钱了,上次一个女知青要给他600元钱,他死活不要,说要钱干什么。有的则说,杨癫子这下发财了。
听着这些人的议论,看着杨顺崇笑嘻嘻地数钱的样子,我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人都到这份上了,还谈什么发财。我们给他这点钱只是我们无奈的一点表示,也许还有怜悯,一半是怜悯他,一半是怜悯自己。除了看到他笑比哭好,还能有什么意义?呜呼,痛哉!旁边的雨晴,早已是泪流满面。
天下起了毛毛细雨,镇里来人传话说都跟村里联系好了。我们说请他们稍等一下,我们要一直走到甘棠坳的尽头。
在原公社食品站前我们停住了脚步。食品站已经不再收猪卖肉了,早已改作他用。巷子口虽然摆放了好几个卖肉的摊位,可是卖的多买的少,只能任人挑肥拣瘦。以前可不是这样,当我们急匆匆地把派购猪抬来,(生怕灌进猪肚子里的潲会因为耽误久了变成粪尿流走,流走的都是钱啊。)到了收猪的人面前,他却随意地就扣除多少斤潲,惹得我们大怒,有时都要动武。好不容易送脱了猪,拿到了一个可以买几斤肉的条子,到了卖肉的面前,他又是想给你哪块是哪块,没有你选择的余地。
富裕中农在食品站这里指指,那里点点,来回拍照,并埋怨说有一次他们送来的猪被扣多了潲。我想也是,他们生产队在山冲冲里,比我们要远多了,送猪的人累得汗流了很多,猪的屎尿也流失的多,如果潲再被扣得多,真正是岂有此理,难怪他要耿耿于怀了。
高出地面几个台阶的那幢大房子,就是当年的供销合作社,相信每个甘棠知青都对它非常熟悉,每次赶场可能都要光顾一下它。那里有我们称为“瓦片子”,农民称为“糖”的饼干。有我实在缺油水了,就咬牙花2块钱买一瓶的红烧肉罐头。有我们为了佐餐花5元钱买200块一坛的豆腐乳。当然还有花花绿绿的布和其它很多农村常用的东西。
可别小看了这供销社,它不仅仅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商店,在有些被繁重的插秧,收禾,砍柴等农活累得精疲力尽的知青眼里,它还是一个最让人向往的工作单位。在里面当一名营业员,就是不少知青最现实可又没法实现的理想。我想像不出,现在的“步步高”等大超市,长沙的“平和堂”等大商厦对求职者的吸引力,是不是会超出当年这个公社供销社对人们的影响。
甘棠公社的卫生院现在成了幼儿园,我们在门口徘徊良久,终于没有进去。以前,没有进过这个卫生院的可算是金刚体了。割禾割破手指的,摔伤的,头痛脑热的,还有那要命的“勾端螺旋体”和不明原因的吃喝不香,日渐消瘦,被说成是中了“蛊”的,都把这个卫生院看作是救苦救难的求生圣地,到了这里就有了安全感,病痛就少了三分。
有次我下楼时,那架单梯子突然断了一根横档,我一下子摔下去,挂在了梯子的下一根横档上。一时间眼冒金星,气也喘不赢。我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我想起单方上讲喝童子尿可以治跌打损伤,于是要围观我的小男孩赶快拉尿。谁知小孩们都吓得跑开了,他们的家长大概也是迷信小孩的尿给人吃了,对这个小孩不利,也不置可否。我当时气恼地想,他们的小孩拉了屎不是都叫狗来舔屁股吗,影响了什么吗?一泡尿就不行吗?没有办法,不能强迫,只好一步一挨地走到公社卫生院。当我哼啊嗨啊地向医生诉说经过,并说我耽心肋骨骨折内出血,现在胸、腹腔里都是血了。医生拿开了听诊器,轻松地对我说,要是你胸腹腔里都是血,你还能走着到卫生院来?我郑重其事地问他,能肯定吗,不会误诊吧。他笑着说,只是软组织有点肿,没什么大事。听了他的话,我一下子好多了,对自己锻炼身体以至身体有较强的抗摔打能力也表示相当的满意。
公社卫生院前面有座小石桥,富裕中农早一向在网上发过一篇“甘棠坳的小石桥”,现在记忆中的石桥就在面前,能不激动?呵呵,念想也都看过他的这篇文章,于是他们三人又是在桥上照,又是在桥下与洗衣服的妇女一起照,忙个不亦乐乎。
富裕中农记忆力的确不凡,照着照着,他觉得不对劲,这个桥的方向好像不对。一问卫生院前面的住户,果不其然,前几年修路的时候,为了路的走向更好,把原来的桥拆了,在改了道的小河上又重新建了这座小桥。桥的式样与原来一样,砌桥的大部分石料也是原来的,难怪大家像西游记里取经的唐僧一样,急着想看到雷音寺,结果把小雷音寺当成雷音寺了。
这个小桥的位置我是记不清了,但我站在桥上,却清楚地记得沿哪条路是通塘头,走哪条路是往溪口。望着前方细雨朦朦中的塘头,再向右边望望那同样模模糊糊的溪口。唉,什么事总是要留些遗憾。如果时间允许,我真想到我曾拿兔子与知青同学换北京鸭的那个塘头×队去看看,到我走小路去靖县县城要经过的溪口去瞧瞧。
镇里又传来话说,富裕中农要找的那位老友也到了。我们一看,时间已近中午,实在不便耽误镇里领导太多的时间。再说,一个甘棠坳就使我们心情激动,流连忘返,那到了生产队,见到了几十年不见的乡亲,又会是怎样一种情景?要多少时间才能平复火一般的激情?心潮起伏,我们快步往镇政府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