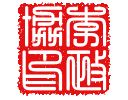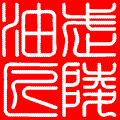母亲门上贴着绿对联
乡下过春节的主打节目是吃团年饭。我当知青的南洞庭湖区吃团年饭是在除夕清晨,要吃完才天亮,而其他地方则多数是除夕晚上,即一年中的最后一餐。一九六九年春节,这个不同的风俗倒是成全了我,早上在住户冬爹家里团年,算是响应了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一起过春节的号召;晚上则可赶到百里之外一个叫干塘坳的地方,和被遣送在那里改造的妈妈一起吃年饭,不让妈妈过年也孤单。
腊月二十八、九两天,我抓紧完成了为全大队贫下中农写春联的任务。除夕前夜,陪着冬爹烤树蔸火,直到被烟薰得实在熬不住了才上床,躺下去很久眼睛还火辣辣地直流泪。我翻来覆去,听着窗外的阵阵北风,暗暗祈祷着明天能有个好天气。
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北风的呼啸变成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只见一长串“牛鬼蛇神”被造反派押着蜿蜒而来。草绳反捆着双手的“牛鬼蛇神”们个个头戴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黑牌。突然,我看见了一个剃去了半边头发的女人,她耷拉着脑袋,剩下的半边头发披散着,在胸前写有“漏网地主”的黑牌上飘荡。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再一次响起时,一名戴红袖章的大汉赶上一步揪着她的头发往后一摁,天啦,原来是教我们高一数学的舒老师!可那张在讲台前尤为靓丽生动的脸已变得苍白如纸,漠无表情。我揉了揉被泪水模糊的双眼,谁知再睁眼看时,那张脸竟变成了我的妈妈。更奇怪的是,梦境居然也有蒙太奇式的截换,瞬刻之间,眼前的场景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天下着鹅毛大雪,河里结着厚厚的冰,挂着黑牌的妈妈在河对岸向我招手,我索性从冰上滑过去,眼看着快要拢岸时,突然冰块塌裂,我跌入了一个漆黑冰冷的深渊,浑身上下似乎有千万把利刃在扎着。在疾速下沉的昏眩中,忽然有一只大手抓住了我,猛一惊,醒了,原来是冬爹掀开被子拉我起床吃年饭。
我回过神来,一骨碌跳下床,趿着鞋跑到屋外看天气。天黑得象被一口锅严严实实罩住,伸出手,没接到雨和雪,这才嘘了一口气,瞌着牙抖着腿回房穿衣服。
堂屋宝书台上点着一盏马灯,两边墙上还各挂一盏美孚灯,屋正中的团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大钵小碗。冬爹郑重其事地开大门放了一卦千响爆竹后,全家老小关门入席。主菜是一大钵整鸡整鸭和猪肘合蒸,碗装的分别是腊肉腊鱼粉丝芋头之类,孩子们盼了三百六十多天的团年饭果然极为丰盛,可惜大家都还是睡眼惺忪,我喝了两盅谷酒,吃了一碗红糖糯米粑粑就吃不下了。
我放下碗筷出门看天,还是伸手不见五指,冬爹说顶多是寅卯交关,又拉我烤火、抽喇叭筒、喝姜盐茶。
冬爹的儿媳我喊刘妈,是位极贤慧的家庭主妇,我身上的大布里褂就是她缝的。她把帮我腌好的队上分的十来斤鱼取出来,又从自己家里取出一条腊肉、一团糯米粉、几支湖藕,分别包好,再一并用个化肥袋装着,用麻绳系紧。冬爹找出一个废窝锹把插进系袋口的绳套中,让我扛在肩上。我从墙上取下斗笠戴好,含着热泪道过别,出门赶路。
天依然漆黑,我在禾场中站定,使劲闭上眼,再缓缓睁开,依稀辨得出路了,便试探着开步。虽然孤身一人,但远近不时有鞭爆声响起,倒也不感寂寞。加上好歹锻炼了三个多月,十多里溜溜滑滑的渠道路总算没有摔跤。赶到船码头,天已大亮,雨也停了。接着便是上划驳,荡到江心上轮船,下了轮船赶汽车,下了汽车再步行,终于在下午四点多汗流浃背地赶到了干塘坳。
干塘坳是个聚居着三四十户人家的老屋场。屋场北面是一道灌木稀疏的小山梁,简易公路从山梁上绕过,进屋场的大路在南面。我沿公路走到屋场北面山坳边,认准了妈妈的住所,反攀着树枝下了山坳,在比我高不盈尺的屋檐下,轻轻敲了敲裂着几道缝的木门。
妈妈又黄又瘦的脸上眼袋下垂,皱纹增多,头上出现了绺绺白发,五十几岁的人显出了六十几岁的苍老,唯一庆幸的是,妈妈没有象舒老师那样被剃去半边头发。
妈妈揉揉眼,定定地盯着我,嘴唇抖动了许久才说出话来:“你来这里干什么?在湖区过年不行吗?”我没有回答,也用不着回答,关上门放下袋子,急切地打量妈妈的生活环境。
牛栏改成的屋子被半垛墙隔成前后两间,后半间屋顶上两片发黄的明瓦和北面一个糊纸的小窗透进些光亮,窗下一个土砖灶,灶前一截树桩当烧火凳,间墙边一个火桶架上座块木板当饭桌,土砖支个纸箱当碗柜,屋檩上吊下一个麻线穿竹杆做成的几层三角架搁放着菜碗,外加一缸、一桶、一面盆,这便是厨房兼饭厅。前半间南面一窗一门,斗窗栅栏和门缝都糊着白纸,靠间墙是架平头木床,白帐白被白垫单一尘不染,床头一个木衣箱、一把扎了不少麻绳并垫着棉片的竹躺椅、外加四把靠背椅,这便是卧室兼客厅。一切都跟一年前一样,没有丝毫改善。
妈妈把我让到躺椅上坐定,忙着打水、倒茶,还象我小时候玩疯了回来那样,将手插进我后衣领摸摸,发现我背上又凉又湿,慌忙拿过干枕巾帮我从衣摆下塞到背上铺平。
妈妈一边忙这忙那,一边不断发问:农活吃得消吗?肚子吃得饱吗?住户好不好?有不有血吸虫等等。我一边洗脸洗脚一边回答,倒掉洗脚水后才将化肥袋拿来解开。
妈妈看到我从队上带回的食物和从县城买回的一瓶葡萄酒及一卦五百响鞭炮后,竟然抱怨起我来:“你真是胆大包天,带这么多东西来,放也没处放,鱼也晒不得……”
“您也真是,又不是偷的,晒几条鱼也犯法吗?”我感到委屈。
“你不晓得,这里今年又减产,户户超支,有的户过年都买不起肉。你要是还有鱼晒出去,有人会说你还是过地主生活。”看来,妈妈的抱怨不无理由,没想到我确实给她背回了一袋子麻烦。
窗口和屋顶的明瓦渐渐变暗,妈妈外出了一趟回来,急忙动手做年饭。她告诉我刚才去了五保户李奶奶家,接她和孙子来我家团年。
我坐到树桩上烧火,妈妈边做菜边向我讲干塘坳的情况。她讲到李奶奶七十一岁了,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儿媳改嫁,留下个有哮喘病的孙子与她相依为命,经常吃了上餐愁下餐。
还讲到一位中年妇女,说我应该称她爱婶。爱婶是一位铜匠从湘潭娶回的大家闺秀,她不喜欢跟屋场里骂骂咧咧的堂客们打交道,三天两头跑来和妈妈说话,总劝妈妈要想开些、看远些。
妈妈还介绍了生产队长,说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队上威信极高,平时对妈妈很照顾,只在农忙时安排做点不下水的活。还总是背地里对妈妈以老师相称……
当我被烤得满脸发烫时,妈妈将年饭做好了,李奶奶也由孙子搀扶着来了。
李奶奶腊黄的脸上布满皱折和老年斑,昏花的眼里噙着浑浊的泪水,稀疏可数的花白头发象个麻网罩在头上,青灰的大面襟棉袄在油灯下漆一样反光。
我恭恭敬敬地搀着她在饭桌前坐下,她从衣襟里扯出一团皱巴巴的手帕,挤干眼眶中的泪水,眨巴几下眼皮后伸长脖子凑过脸来打量我:“好角色咧!天庭饱满,地廓方圆咧!会有出头咧,会……”
我傻傻地不知该怎么回答,好在妈妈赶紧解围:“您快莫乱讲,什么出头不出头,他也在当农民咧。”
“好人总会出头咧,只是出了头,要拿只眼睛照看一下你这个可怜的侄儿咧!”李奶奶边说边把缩在身后的孙子拽到我跟前,叫他减叔叔。
孩子叫立人,十四岁的年龄,才长成正常孩子十岁的个头,佝偻着背,菜色的脸上深嵌着两个大眼窝,眼珠木木地盯着我。突然,只见他脖子上暴起几根青筋,接着是一阵喘不过气的猛咳,好不容易止住咳,回过气,这才胀红着脸腼腆地叫了我一声叔叔,并挤出了一丝笑容。
李奶奶见孙子咳完了,叹了口气,又唠叼起来:“你这个侄子造孽咧!五岁死爹,没天良的娘就丢下他出身了,哪象你妈妈,守寡几十年带大你咧!”
“看您又扯远了。”妈妈一边端莱一边阻止李奶奶的唠叼。
可李奶奶的话并没有打住:“唉,如今的人就是咬着舌子讲话,冒天良咧!你娘老子一直教书,现在反过来硬说她是地主,今天上午还喊到大队部训话……”
没等她讲完,妈妈端着菜没来得及放上桌,慌忙用手肘碰了一下李奶奶,抢过话头说道:“您没搞清楚,上午我是买年货去了。”
李奶奶瞪着眼看看妈妈又望望我,终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随着妈妈手上的菜放下,老太太的视线被牵引到了桌上。
看到满桌的佳肴后,她兴奋得又是缩鼻、又是夸赞:“有鱼有肉还有红酒咧!这才叫过热闹年咧!”但她突然想起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有爆竹吧?要放爆竹!”
我也记起了早上冬爹放鞭炮的场景,也记起了特意买回的那卦千响鞭炮,立马说了个“有”字并起身去拿,但被妈妈阻止了:“我们这种人家还放什么鞭炮嘛,别人会笑话。”
可李奶奶不依不饶:“亏你还是教书的,过年放爆竹是驱邪咧!象你这样遭冤枉的好人更要放!”
妈妈拗不过,更怕李奶奶越说越出格,便起身去拿,摸索了好一阵才拿出几寸长的一截鞭炮来,并向我作了一个别吱声的手势。正好这时隔壁响起了鞭炮声,妈妈立刻催我和立人打开后门点燃了鞭炮,噼叭几声,眨眼间就夹杂在隔壁的鞭炮声中响完了,总算是完成了团年饭不可少的鸣炮程序。
吃完年饭,李奶奶由打着饱嗝的孙子搀着,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顿饭给我留下了两个悬念,一个是上午妈妈被喊去大队部训话的事,由此还想到平日被监督、被运动的情况。但这个话题到了嘴边又咽下去了,我想应该给妈妈留份好心情过年。另一个悬念是鞭炮的长短问题,这是可以问的,便急着问妈妈千响鞭炮怎么只有几寸长。妈妈神秘地笑笑:“我剪断了,能意思一下就不错了。”
妈妈收拾了团年饭的残局后,将桌子移到前屋,拿出一包水果糖和一包扣子模样的胡椒饼放在桌上,再从灶里夹出一盆火匙(未燃尽的柴杆),并将椅子摆放整齐。“有客来吗?”我问。
“小孩子会挨家挨户送恭禧啊!”妈妈兴奋地回答。
除夕之夜,孩子们成群结伙,打着灯笼挨家挨户高喊“恭禧恭禧”,是当地过春节的一个重要节目。就大人而言,是讨个吉利,就孩子而言,是讨个零食打发。妈妈当年在农村教书,是极重视这档节目的,唯恐让孩子们扫兴。
果然,妈妈准备停当后,窗外就晃过来几团亮光。妈妈满面笑容地朝前门走去,但敲门声并没有响起,只见几团红光在门缝外晃动,我起身走到妈妈身边,听得孩子们在外面七嘴八舌地议论:
“这里是绿对联!”
“ 老--实--改--造,重--新--做--人。”
“贴红联是好人,贴绿对联是敌人。”
“不能跟敌人送恭禧!”
“……”
妈妈退回几步,重重地落坐在床上,发呆似地望着几团亮光从门缝和窗口消逝,喃喃说道:“你何必回来嘛……”
我缓缓走近妈妈,轻轻地把她搂在怀里,将脸偎到她头上。我想安慰她,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话,只有眼泪夺眶而出……
“砰!砰!”突然听得有人在敲后门,妈妈警觉地站起来朝后门走去,我紧随其后。
后门的缝隙中晃着两团红光,妈妈的手停在门扣上,等到门再次被敲响,这才把门打开。
两个男孩各提一盏灯笼挤进门来,齐声朗诵一般:“恭禧!恭禧!恭禧傅奶奶过热闹年!”
妈妈兴高彩烈把孩子迎到前屋,接过灯笼吹熄、放好,先是隆重将我推出,要孩子们喊叔叔,然后向我介绍:虎头虎脑的八岁孩子叫乐乐,是队长的儿子;斯斯文文的十岁孩子叫健健,是爱婶的儿子。
“傅奶奶门上贴了绿对联,你们不害怕?”我同时挽着两个孩子问道。
“我不怕!我妈说傅奶奶是她最尊敬的人!”健健回答。
乐乐的声音更大:“我更不怕!爸爸说傅奶奶是受冤枉的好老师!”
我万分感激地将两个孩子紧紧搂在怀里,抬头看妈妈,只见两颗晶莹的泪珠正从她眼里流出……
“今晚你们送完恭禧还守岁吗?”妈妈一边往两个孩子的口袋灌糖果,一边笑着提问。
“守岁咧,要守圆岁!”孩子齐声回答。
“那我给你们一样东西玩好吗?”妈妈边说边起身拿来了那卦剩下的鞭炮,并将鞭炮对折后逢中剪为两截。两个孩子乐呵呵地同时伸手去接,妈妈却两手一举,低头问道:“你们打算怎么放呢?”
“点燃一丢呀!”乐乐抢着回答。
“那健健怎么放呢?也是一次就放完它吗?”妈妈启发健健。
健健眨了眨眼说:“我拆散一个个放。”
妈妈满意地点点头:“健健这个主意好,又好玩,又玩得久。乐乐你也这样放好吗?”
待乐乐顽皮的点头默认后,妈妈仍没有将鞭炮立即分给孩子,而是从枕边取出老花镜戴上,教孩子们一个一个地将鞭炮拆散,同时又交代他们不能捏在手上放、不能对着柴垛放等等。
鞭炮全部拆散包成两包交给孩子后,我将灯笼点着送到孩子手上,妈妈开门,直到看着他们连蹦带跳地走远才轻轻关门。我迎上去从背后抱着妈妈的双肩,妈妈回过头来望着我笑了。
从妈妈的笑容里,我读出了几分欣慰,也读出了几分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