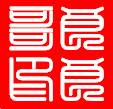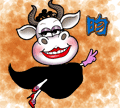犟牛兄:
我今天终于收到了<靖县知青文集>.收发室的小姑娘调我的口味:朱老师,你的情书来了!一看是您国庆节时寄来的那本.很高兴,今夜无眠了!
您费心又寄一本,我准备送给我的弟弟.他是长沙一中毕业的.到靖县去过.后来到黑龙江插队,也算是一名老知青了.常看我们的网站.附上一篇小文,算是做个介绍吧.
谢谢您!
朱纪飞 10月19日
我的弟弟
我的弟弟小我三岁,我下乡时他还在一中读书。虽然文革后期读书还未完全走上正规,但也算还在上学。据说有政策,家有一个下乡的另一个孩子可以不下乡。(我家就两兄弟)但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家庭就享受不到了。一中初中毕业后,街道上督促他下乡,我母亲欲哭无泪,准备把他送到东北我父亲那里去。当时我父亲还在黑龙江劳动,一家四口分为三处。考虑将来全家团聚是不可能了,一位老人身边留一个吧。
临去东北前,我弟弟提出想到靖县见我一面。家里同意了。给我写了信约好哪天到,让我去接。到了他该来的那天,我因舍不得那十分工分,出了一天工晚上才到县城去接他。当时靖县有三个旅店:县招待所、大众旅社、国营旅社。天已经黑了,我和段兄打着手电,挨着旅社找。哪都没有,这可怎么办?我老弟还是个孩子,从没出过远门,丢了可如何是好!找到第二遍,我忽然在旅社登记簿上看到一个我熟悉的单位名字:中国农科院,我对段兄说,就是他。接待员说:你们找了半天长沙来的学生,怎么又变成北京来的干部了?上楼一看果然是,此君早已蒙头大睡。原来父亲是右派,回家路上不方便,在北京老单位托人开了一张介绍信,这里用上了。众人晒笑:那有你这样乳嗅未干的、北京来的外调干部,还拽普通话,让旅社服务员高看一眼,安排了个单间。
一路无话,回到腰古坡。当地民风质朴,远道来的亲戚家家要请吃饭。一日,老队长请吃饭,让老弟坐上席,他不懂规矩,一屁股坐上去。当着主人面我们又不好说,团里的长辈,几个知青都成了陪客。上菜时有一碗面条。老弟一见,眼睛放绿光,心想:这几日老是吃米饭,嘴里淡出鸟来,可见到面食了!一把端过来说:你们莫客气,我就吃这碗面算答。孰不知,在乡里面条是稀罕物,待客才煮一碗当主菜的。闹了一个笑话。
到了山区,自然要上山看看。老弟对走山路拿一根把棍很感兴趣。我告诉他,把棍的作用不是协助走路,是扫草里的蛇用的。他更来劲了:蛇?在那里?甩着把棍神气的很,一副《渡江侦察记》里敌参谋长的样子。一不小心,把手表甩到蓬槛里去了。两个人撅着屁股找了半天。老弟一定要看看我守野猪的“窝棚”,好奇的很:咦!还是竹铺子啊,舒服的很嘛。我带他在野猪棚子边烧了一堆火,烧核桃吃。真是惬意的很。
当时没有旅游的概念,也算是他下乡前的一个休假吧。后来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老弟下放到中苏边界的一个村子里,冰天雪地,吃高粱米,吃了不少苦。一家四口分四个地方。直到父亲平反后才上大学,工作。至今仍留在了东北成了一个真正的北大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