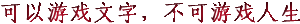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硬伤”与“软伤”——读书偶得
上网查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资料,见清废帝溥义封其谥号“忠悫公”一节,言及友人陈寅恪等为其自沉后治丧等事。内中特别在“恪”字后标拼音que(第四声),并附注因陈先生系客家人而客家话读“恪”为que,故陈寅恪先生名之“恪”依客家话读此音;但又言,亦有人依常读“恪”为ke,先生亦认可。翻《新华字典》,“恪”字只有ke读音;翻《辞海》,除了“恪”字读音ke,另有括号(旧读que)。看来网上有些资料也如人们常说的“硬伤”,如此例注明陈寅恪先生之“恪”依旧音读que即可,怎会因国学大师陈先生是客家人读“恪”为que,圈子里人就把此字读que呢?
说到此,不免有点汗颜,半年前与知青网朋友在中大聚会,席间朋友谈起曾去附近陈先生故居遛达,我就是把大师名字中“恪”读ke的,足见自己“附庸风雅”而不“雅”也!好在当时觥筹交错,一些对国学深有心得的朋友如破衣先生在嘈杂的餐厅未听清,否则破衣先生早就会象往常一样暗暗在网站短信里提出“非议”了。
不过又有些为陈先生悲哀。这样的“硬伤”把一位颇孚众望的学界巨子弄得象学阀一样,好象他家乡客家话读此音,这个字就要读此音……那不也象武则天硬为自己的名字造出个曌字一样霸道?当然还有比武曌更霸道的“硬伤”,过去为避帝王讳,硬是生生把家谕户晓的名词更改,尽管历史往往又恢复了其原称。偶翻《古文观止》见“武帝求茂才异等诏”,后注云:“茂才,秀才。后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讳,改秀才为茂才”。说起“茂才”,现在有几人知是何物?但说到“秀才”,可能三岁小儿都知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
至于汉字读音不按常理出牌,大概还有首都的一些地名才有此资格。如前门的大栅栏,外地人见街牌“大栅栏”三字,一般会读成da zha lan,可北京人就是牛,这三字读da sha la,而且字正腔圆的央视主播也要循此例。有些汉字读音的变化人们巳习以为常了。如“叶公好龙”,谁还会把“叶”读she呢?可这故事发生在古代she地,不读she巳失去其成为成语的渊源。“大夫”有几人还把“大”读dai呢?可这大夫不唯是古代大臣之称,自宋把官内医官设大夫以下官阶民间又把医生称大夫,许多人叫成了da fu。不过,这些巳被社会广泛认可的“硬伤”少人置疑,是否可称“软伤”了?
大概拼音文字无此一字多音现象。英语Rose就是读Rose,White就是读White。当然,一字多义中西皆有之,如Rose既是指玫瑰,也可用作人名露丝;White既是形容白色的,也用作人名怀特。拼音文字中护照人名大概不会出现此现象:有某人重阳节前后生,长辈为其取名重九。7年前赴俄罗斯旅游办的护照英文名为拼音chong jiu,前2年赴欧洲办的新护照英文名就打成zhong jiu了……如果外国朋友同时看到这2本护照,大概真要“判若二人”了。
最多的“硬伤”,当然是如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理水》中批判过对历史人物的硬伤(有的版本曾指名道姓言鲁迅是讽某知名教授“禹是一条虫”说):
“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吗?”
……乡下人站起来反驳学者,“人里面是有叫作阿禹的”,“况且‘禹’也不是虫,这是我们乡下人的简笔字,老爷们都写作‘禺’,是大猴子……”
“人有叫大……大……猴子的吗?”学者跳起来了,连忙嚥下没有嚼烂的一块洋面包,鼻子红到发紫。
“有呀,连叫阿狗、阿猫的也有。”乡下人回答。
……
七十余年过去,鲁迅先生笔下对历史人物“硬伤”的故事仍跃然纸上。
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等书90年代末一炮走红后,我曾循书中足迹踏访敦煌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17号窟,去宁波观“天一阁”,赡都江堰青城山二王庙……自从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与《山居笔记》走红以后,批评的文字也不少。某著名出版社出了本既有热评也有批评的专集99年版《余秋雨现象批判》。总以为言之凿凿,翻了一下就束之高阁。写到“硬伤”,心想当时这本书有许多评余先生“硬伤”处,何不引用一下?随手一翻,觉得有些刺还是挑得挺细心的。如周先生评《文化苦旅.阳关雪》中“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周先生说,“天呐,您真是在‘人头济济’的场合‘摸’向寒山寺的吗?您是在‘摸寺’还是‘摸人’呢?”灯火读到此也不免要附句不恭的话,人们往往用“人才济济”形容人才云集,而对拥挤的人群一般是用“人头攒动”之类词语形容。
梅先生的文评就不敢苟同了。他评《山居笔记.十万进士》时指出,余先生在此文中将本是进士的王维、贺知章“点”了状元,是一大“硬伤”。我瞪大眼睛把书柜《山居笔记》中《十万进士》一文读了2遍也未找到言王维、贺知章“点”了状元之句,只有引《集异记》“歧王看重王维之才,荐与公主,向考官打招呼,成为京兆尹上报第一人……”京兆尹上报第一人有望点状元,但不是巳点状元。文中更未见贺知章名,看来评者未细读此文,所论是对余先生的“硬伤”了。未必我们读的书不是一个版本?俺可是8年前在市内最大的书店花了30大毛买的正版。
还是前面提到的周先生,对余先生的《文化苦旅.洞庭一角》评道“硬生生把虞舜与娥皇、女英的夫妻关系改编成父女关系,使迷人的‘湘妃竹’传说退化成与爱情无涉的孝悌故事。”也许周先生提到的是传闻余先生曾于1999年夏在千年岳簏书院“设坛论道”谈娥皇、女英为舜女儿的口误,翻开手头1996年版《文化苦旅》,赫然写着“……君山还是一派开放襟怀。它的腹地,有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忽瑰艳的神话……”没说错呀,毛泽东七律诗《答友人》中曾咏两位帝子本就是尧之女儿,舜之二妃呀!如果对“人头济济”评得有见地,此处论者还未细看原文即加评论,却是“硬伤”了。本想引为评余先生“硬伤”的例子,幸好认真翻了下原著,否则也要贻笑大方。
有些论者未及细读原著即滥加评论,正是现在一些人做学问急功近利的急躁体现。不唯原著作者,想必许多读者细究这些文字也有种“很受伤”的感觉。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大概余先生也有几分感悟,他在《十万进士》中评那些科举主考官“你曾经引为自豪的全部学问背后,可能都掩藏着一个个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