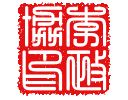初下洞庭
1969年元月五日,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对我来说,却终身难忘:我,一个涉世未深懵懵懂懂的小青年,身穿母亲亲手改制的黑棉衣,肩上斜挎一黄包,内放几本书及换洗衣服,一床薄薄的棉被和一床薄薄的毛毯捆成井字型,很贴切地背在背上,登上了由长沙开往南县的轮船,只身一人到 妹妹的知青点---沅江县新华公社扦队落户.
清晨6:00,汽笛一声长呜,轮船在寒风中徐徐地离开了码头,沿着北去的湘江,顺流而下.我安顿好自己的仓位后,从底舱走到了船尾的甲板上.天渐渐亮了起来,周边景色也清晰起来,我怀着好奇新鲜感极目远眺:在灰濛濛的天空下,江面上、帆船点点,往来穿梭;沿江岸边,高大的烟囱,密集的房屋,熙熙攘攘的人群,城市的轮廓迅速地向后倒去;青葱的菜地,宽旷的田野,镜似的水塘,互相交换着,目不暇接.三叉机、铜官、靖港---,一串串熟悉的地名飞逝而过.船到临资口,江面逐渐宽阔起来,进入漉湖之后,虽然是枯水季节,但浩渺的湖面仍碧波荡漾,船在平静的湖面,犁开一道深沟,白色的浪花翻腾雀跃,间或扑上船舷撞成碎片.远处的滩涂上,杨柳成片,芦丛耸立,偶尔可见低头吃草的牛羊和觅食的水乌.航行十余个小时后,傍晚时分,航班终于到了目的地---茅草街.
人流匆匆散去,我问明了去草尾镇的方向后,与同船的另两个知青结伴而行.幕色苍茫中,沿着十里长堤到了草尾镇,在临河的一个客店息歇下来,睡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我独自一人乘船渡过草尾河到了新华公社,一问,从公社到三码头还有二十余里地,虽然具体位置不知,但我用上了最可靠的方法:路在嘴边.一路上,我不知问了多少人家,临近晌午,我到了自己的目的地---均利大队11生产队.但不巧,知青点上空无一人,据说她们随劳动力到柴山砍柴去了.
冬闲时节,农村只吃两餐饭,大队伍支书叫我到他家吃了一餐
便饭,饭是箩卜丝掺着白米做的,抄了一碟白菜,一碟辣椒外,另外煎了两个鸡蛋.饭菜虽简单,但我却吃得津津有味.
之后,临家李婶叫我到她家坐坐,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端庄、贤淑的农村妇女,她丈夫在白沙公社当武装部长,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热情地从尚有余火的灶堂内端出一罐豆子芝麻茶来,冲了一碗给我,热腾腾香喷喷,感觉好极了.直到下午五点左右,李婶的女儿跑来说,青年知识回来了,听罢,我立即起身道谢出门.
从李婶家出来,往左拐弯进入一条小巷,两边都是枝条围成的篱笆墙,离知青点还有十来米时,就听到不时传来阵阵银铃般的笑声,走近一看 ,我不禁打量起这五位十七、八岁的知青姑娘:她们一律身着流行的蓝色半长冬棉衣,脖子上围上艳丽的长围巾,清一色的两条齐刷刷的小辨子,红扑扑的脸上,明目皓齿,充满了青春朝气;与此同时,我也从她们稍显惊异的目光中读懂了自己:中等的个头,略显偏瘦,充满稚气的眼神分明是一个学生伢.
毕竟是他乡遇老乡,一阵寒喧后,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一家人.她们告诉我,自下乡的几天来,因怕鬼、怕狗、怕人,晚上睡觉都是栓门后,还要用桌子櫈子等物顶住门,你这一来,我们就不怕了,听到此处,一股男子汉的豪情充满了我的胸中.
我的床安在堂屋里,夜深人静,我打着哈欠钻进冰冷的被窝筒,呼啸的北风从门缝、从透光的用牛屎糊成的壁洞穿透进来,极具杀伤力,我抖抖嗦嗦蒙头窝在被子中,似醒似睡、朦朦胧胧中熬过了初下洞庭当知青的第一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