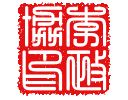1972年3月8日,200名知青驻进了干校,然而,干校并没有作好准备,除了一片荒芜的土地,连住房都没有,知青们只能挤进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干校本来是干部劳动的地方,一下安置这么多知青,显得难以应付。然而知青们用自己的双手,开始了改变干校面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一天天地把干校建设成自己的家园。以下是对干校生活点点滴滴的回顾。
当务之急
干校当务之急的是两件事:一是住房,二是通电。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我们开始打砖盖房,没多久,我们就盖起了一排土坯平房,这种房子冬暖夏凉,属于典型的经济适用房。同时,我们还要解决电的问题,由专业电工确定拉电路线,然后我们就翻山越岭把线路上的灌木砍掉,再运送电杆,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通电了,从而结束了煤油灯的历史。其他基本设施也在一项项地建设,如修路架桥,兴修水利,我们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就修起了一座水库,第二年我们的梯田就做到了旱涝保收。
打篮球
当时打篮球是一项非常普及的运动,尤其是男子汉们,几乎没有不会打篮球的。于是修建篮球场成了知青呼声最高的事情。说干就干!我们从小河里运来了卵石河沙,和上水泥,一个场地就打好了,篮球架是用木头做的,山上有的是大木头。球场修好后,我们经常进行比赛。我们球队的水平相当高,有几名队员曾经是县球队的,如许永刚,梁瑞郴等,许永刚弹跳好,善投空心篮,梁瑞郴速度快,善投擦板篮,因而,我们的球队打遍鲤鱼塘无敌手,看他们打球是知青们最开心的时候,观众常常为他们喝彩助威,那兴致一点也不亚于现在看奥运会。
伙食状况
每月发12元的餐票,如不够可自己再购买。人多食堂小,买饭时拥挤不堪,有时免不了发生冲突。平时餐餐吃小菜,每月逢十才能吃荤菜,也就是每月吃三次荤菜,由于劳动强度大,我们吃得特别多,我一餐吃过一斤,有的女知青一餐竟然吃过一斤二两。每到吃好菜的时候,我们都要打双份,再打上几两酒,美美地吃它一顿。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善自己的伙食,有一次,我和另一个知青中午不休息,到水渠里去摸田螺,不大一会,我们就摸到一桶,晚上我们就煮起来吃,不料,田螺的香味四溢,把中队的陈队长引来了,于是我们三人痛快地吃起来。
文艺宣传队
在当时文艺宣传队与篮球队是一对孪生兄弟,任何一个单位,一个团体,都有这两支队伍。我们的宣传队水平也是比较高的,我们有创作人才,乐器人才,表演人才,创作主要由我与梁瑞郴担任,我们各自创作了一个剧本;乐器由我,梁瑞郴,赵忠平等来演奏,演员有曾玲玲,戴葆英等。每逢重大节日,我们都要进行演出,我们在球场上搭建一个宽敞的舞台,用火把照明,载歌载舞。记得我们的宣传队还参加过县里的一次文艺汇演。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就是这样用青春的热情,创造欢乐,自娱自乐,度过那难忘的时光。
蛇灾
如果说鲤鱼塘是一个多蛇的地区,那么,干校就是一个蛇窝,我们出门就见蛇,路上可遇到蛇,水里可看到蛇的游动,树上可看到蛇鸟大战,即使呆在寝室里,蛇也随时会从窗户探进头来向你打招呼,有一次,我竟然从床底下发现了一条大蛇,我吓得跑出了寝室,胆大的黄晓毛操起一根扁担,把那条一米多长的蛇打死了,我们都非常担心被蛇咬伤。然而,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73年6月9日晚上,女知青宋曼玲就寝前去水渠边洗脚,不幸被毒蛇咬伤,校领导马上联系鲤鱼塘公社医院,然而被拒之门外,我们用尽了种种办法自救,仍不能挽救宋曼玲的生命,就在这天夜里,在人们的酣睡中,宋曼玲同志走完了她十九岁的人生,永远离开了她深爱着的这个知青集体,离开了这个她还没有看够的人世。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多蛇地区的医院,为什么不配备治疗蛇伤的医生和药品,为什么把一个明明可以抢救的病人拒之门外呢?我们的医院里都写着一条大红标语:“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把一个不抢救就必死无疑的人拒之门外,这难道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眼看着一个鲜活的知青的生命在绝望中消失,当时永兴县主管卫生系统的领导,以及鲤鱼塘公社医院的院长,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吗?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面对长眠在那片土地上的死者,这两个人将永远受到良心和道义的谴责,历史,不会原谅他们!
养狗趣谈
在干校除了打球,也没有什么可玩的,大家觉得养狗很好玩,于是便争相养起狗来,大大小小的狗养了几十条。这群狗对知青很友好,对外人却毫不客气,有一个上山割松脂的老乡天天从干校经过,每次都要遭到狗群的攻击,那老乡也不畏惧,挥舞着割脂杆与狗群交战,精彩的打斗引起知青的围观,那场面仿佛古罗马斗兽场的表演。
我也喜欢狗,童年时就养过狗,在干校也养了一条,那是一条棕色的狗,那狗双耳直立,两眼放光,眉宇间有道金色的斑纹,威风凛凛,我唤它叫“拉菲克”,这名字来自马季的相声《友谊颂》,就是“朋友”的意思,我给它脖子上挂一个用灯泡屁股做的铃铛。清晨,“拉菲克”与我一同出工,干活时,“拉菲克”就在草丛里腾跃撒欢,捕捉那些蚂蚱,青蛙,四脚蛇什么的,收工时,我一声口哨,“拉菲克”便闪电般扑向我,一路撒下清脆的铃声。
尾声
1975年6月的一天,我坐上一辆手扶拖拉机,离开了干校。光阴似箭,三十多年过去了,然而,干校的一切却仍然清晰地储存在记忆里:那山,那溪,那古松翠柏,那水库,那梯田,还有那芳草萋萋的知青墓,挥之不去,历历在目。
写于2007年7月8日离开干校三十二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