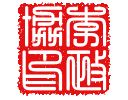据传,我们曹家湾村最早建于清朝乾隆年间。村庄充分体现了湘南民居的特色,依山傍水按天圆地方而建。四方青砖绿瓦房,根根掾头雕刻着福禄兽,将天赐福禄通过天井送到各家各户;外侧“山”字垛逶迤参天,四面蓝灰墙,白灰线,一幅幅古朴书画更加凸现出传统文化;雕梁画栋的“文”字门楼龙凤呈祥,中门顶端骇然三个大字:“七步第”,让人未进门便知这里居住的是“建安七子”曹植之后人。开山祖宗养六子,分上下左右移次而住,秩序井然,相处和睦,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令人不解的是,墨水村4姓族民都没有建立祠堂,最大可能他们都属于同宗的分支,每逢清明祭祖、修族谱等宗族盛事,他们只管出钱出粮,参加祠堂里的全部活动。然而,他们参加宗族活动,只能做些杂事,只能获得坐末席的待遇。更难容忍的是,有一年同宗人公然闯进曹家湾,在众目睽睽下杀死一人,扬长而去。案件不了了之,族人终于反目成仇。加之新中国建立后,封建宗族观念淡化,宗族活动随之消失,祠堂的凝聚力大为削弱。因此,尽管近些年来宗族意识又呈泛滥之势,他们再也不想受此窝囊气,不再参加类似活动,各自在村子里摆酒设宴,处理本村本族事务。由此可见,墨水人身上多少还存在着历史传承的反叛精神。
1958年,永兴县决定堵住墨水唯一的出水口,修建造福香梅公社的水库,墨水洞里的乡亲们分别移居他乡。可一年后县里又撤销水库恢复农耕,乡亲们又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建成墨水新村。新村上下整齐两排,俨然一段街道,活象一个等号,既可看出长幼有序的传统观念,亦可领略平等待人的处世理念。墙上至今还留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标语、图画痕迹,依稀可见“大干、苦干、巧干”社会主义的场面与氛围。
近20多年来,乡亲们的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墨水村半数以上的农民建设了新民居。充满时代气息的新民居与铭刻传统文化的旧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折射出新旧文化的鸿沟。新旧建筑所表现的风格和文化内涵,深深地打下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烙印。
然而,某些方面与其说是进步,还不如说是倒退。
一是民居建设的有序和无序。旧民居体现了“君臣父子”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前栋不得高于后栋,超高便是欺祖;长幼次序分明,次序混乱视为乱伦。新民居则充分显示出独立意识和竞争意识,单家独院,朝向不一,高矮不论,个性突出,打破了传统民居文化的统一性和严谨性。
二是村民感情的亲近与疏远。传统民居基本上是一个姓氏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统天下,谱写着族民世代生存繁衍的历史,乡亲们生活显得和谐相处、亲密无间;新民居一道道围墙隔断了彼此往来之路,淡化了亲情氛围,影响了和谐性。而且,新民居是后生们的专利,旧民居则是老年人的归宿,多少有些伦理失落的感觉。
三是环境资源的负面效应。新民居因规划滞后、建设无序,土地占用量急剧增加,且为良田沃土。墨水村建设同样面积的新民居,比及传统民居至少增加用地一倍以上,造成了乡村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不仅如此,因新民居建设缺乏整体性,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管理面大,管理措施不完善,农机农械农具乱堆乱放,生产生活废水废气废渣乱排,有机废弃物处置不科学、处理不完全,致使农村卫生环境十分恶劣。与此同时,旧民居因其居住人口急剧下降,逐步成为“空心村”,甚至成了家禽家畜的饲养场所,因而与新民居一同构成环境的“双重污染”和资源的“双重浪费”。
山村居住条件的改善与乡亲们居住环境的反差显得极为明显,亲情、友情与人情逐步显得淡薄。今年台风“碧利斯”袭击郴州,“五百年一遇的特大剧烈气候事件”给郴州市造成了数百人死亡、数十亿元经济损失的悲惨后果。墨水村也倒塌了几间房屋,而且“屋漏偏逢邪风雨”,遭灾的都是孤独老人。一天,村支书给我打来电话,欲借我家全部房屋安置灾民,我二话没说满口答应。放下电话一回味,其中有一位80来岁的老人,他的侄儿建有一座“别墅式”宅院,为什么不把亲婶娘接过去住呢?细想一点也不奇怪,生活浓如蜜,人情淡如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