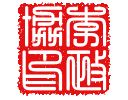她只小我一岁,小时候跟我一般高矮,性格不似一般女孩子文静,和怯弱,倒比一般男孩还要倔强。她最喜欢成天跟着我跑,若 不是 口里"小哥小哥"地叫个不停,别人一定会把 她当作我姐姐的。
虽然有不少人持这种误解,但她从来没有不把我当哥哥的时候,那时我们的父母还在,父亲总喜欢 把邻家的孩子们都叫到家里来做作业,孩子们也很乐意来我家,因为我父亲特别和善,母亲也好客,小孩子们可以常常得到一些平时吃不到的零食。父亲还很乐意辅导孩子们的功课,对答对提问,作业做得好的孩子,还发点奖品给予鼓励呢。来我家最多的就算刘祖茂姐弟,和鲁小兵兄弟了。我们这群孩孑中成绩最好的,耍数我妹妹,和鲁小兵了,所以他们能经常得到我父亲的奖品了。妹妹为了得到我的同意让她跟着我跑,总是把得到奘品分给我,从来不在我跟前趾高气杨。直到现在,我们兄妹情谊都很好,她也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小哥.小哥"的叫着我。
文革时父亲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厄运,并殃及到母亲和我全家的兄弟姐妹,把我和妹妹读初中的权利都剥夺了,我们成了知识青年,被一个一个相继发配到荒凉,偏远的农村,各自去谋生。 我妹妹十六岁多一点就下放到一个偏远,落后的的土家族寨子里,那里人们几乎还过着半原始的生活,主食是玉米,红薯,吃顿大米饭算是侈肴了。人人头上围着一条头帕,走近一点一般酸臭扑面而来,满是头油垢的头帕扔到水里,绝不会下沉的。这里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田间,地头, 劳作。十天,半月,去赶一趟场,要翻过几座大山,早上去,天黑才能回来。
我妹妹在家时最小,大家都有点宠她,在这样的环境下,她默默的承受着这生活给她的艰难,与不幸,居然交上了当地的几个土家族姑娘做朋友呢。
当时我也下放到一个湖乡的生产队,可我却不安份的呆在生产岀工,却像一个唐,吉柯德式的游俠。身无分文,却滿世界游荡,凡有知青下放的地方便有我游荡的足迹。 我游荡到妹妹所在地方看到这里的一切后,心中十分的不忍,回长沙后向父母谈起了妹妹的情况,父母知后心急如焚,好在父亲本来只是技术工程师,又实在查不岀什么问题,所以形势没那么紧张了。我父亲下放在条件稍好一点安乡县,帮一个公社建了个颇为先进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父亲便以这一点成绩把妹妹转到了该公社。妹妹担任了广播员,和文书等职,在当时的那个年代能到公社里当一名工作人员,对妹妹境遇来说是起了个翻天履地的变化了,不用愁吃不饱饭,也不会日晒兩淋了。在这块相对滋润的土壤里,妹妹充分发挥了她吃苦耐劳的优点和工作上任劳任怨的作风,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经常以一颗善良的心,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在当地赢得了一片赞杨之声。
转眼到了七四年,我父亲六十岁了,按当时的政策父亲退休可以由一个儿女耒顶职。当我们全家都来商量着我与妹妹之间,由谁顶职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说:“让妹妹回来照顾爸爸妈妈吧。”
妹妹回来了,妹妹顶了父亲公职,参加了工作,同时也担负照顾父母的责任。 我父亲是个知识份子,好学、上进是他的一贯品格。他对妹妹说“以你目前文化程度决不能适应今后的工作 的,从今后你必须糸统的学习”,妹妹便从初中一年级起开始糸统的学习,所有课程都由父亲亲自辅导,从此妹妹在工作之余开始了兩叁年的刻苦学习。
我偶尔从农村回到长沙过年过节,看到她总是写呀,画呀,算呀,那个年代连电风扇都没有,炎炎的夏天夜晚一把扇子,一条毛巾,一盆冷水,寒冷的冬天,一个热水帒,妹妹凭着惊人的毅力,硬是把文革中落下的初,高中,的全部课程补了上来。还考上了当时的第一届电大,用她的话说,小哥,我爭了这口气。我心中实在佩服她,从那时起我对妹妹有了一股深深的敬意。
转眼又过了三十多年,妹妹已是一名国家公务员,在几十年里妹妹在单位的多个部门工作过,但无论到那里都能得到大家的肯定。现在她己光荣的退休,每天都进行一些康健的娱乐活动,她的歌唱得可好呢,最近还上了湖知网,她看到了好文章还不时的跟帖,说不定她也会写出她的故事来呢。只有一点她还是没变,还总是“小哥、小哥”的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