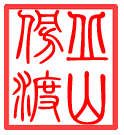“你真的好胡涂,那个台湾老兵能把她带到台湾去吗?他既冇得贼心,也冇得贼胆,他又冇当角色,一个老兵,有什么狠讲?退一万步讲,即算是把细毛办到了台湾,那边还有一只虎视眈眈的母大虫呢,她能有好日子过吗?”话说到这里,于德祥也只有一声叹息,心里想,细毛的命真的是太苦了。韩月球似乎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不再想说这个话题了。正在这时,胡眯子忽然瞥了一眼韩月球:“密司韩,你和德哥讲了这么久的悄悄话,不怕德哥嫂子吃醋么?”
“放你娘的驴子屁!”韩月球说了句年轻时常挂在嘴边的粗话。胡眯子没接腔,却冲于德祥道:“你才和密司韩讲悄悄话去了,我们这里经过研究已经作出决定,还过三年,9月16日那天,我们周塘大队的老知青都到长沙聚一次,地点就安排在华天大酒店,费用和尚扛大头,其余的我们分摊,不要你出一分钱,到时候一定要来呀。”胡眯子一边说,一边解开衣襟,又将雅格尔领带拉拉松。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呀,有的流窜到南京上海去的我都会把他们喊起回来,难得在一起聚一次么。”和尚面带春风,伸出套着大钻戒的手指散着烟说。
“如今和尚早已今非昔比了,自己开了家公司,手下人马成千上万,老婆也换了好几个,还不算漂亮的女秘书。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只管同他讲。”胡眯子嘴里喷着酒气怪笑着朝于德祥说。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只会混说。”韩月球笑骂道,于德祥便有些将信将疑地望着和尚。和尚虽然喝了很多酒,脑子却很清晰:印堂光光亮亮,毫无醉态,一看就知道是常在场面上混的人。“吃烟吃烟,平时见一次都不容易,今天在这方土地上相聚真的是缘分。”和尚又将桌上一盒未开封的纸烟隔着火锅炉子扔向于德祥:“你莫听胡眯子吹,我哪里有那号牛皮,只是开了一家做化妆品生意的公司,手下员工也就几十个,这两年搭帮朋友帮忙,小赚了一点,你要是有什么事情用得上我,尽管讲就是,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和尚虽然不才,道上还是有几个朋友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共一口鼎锅舀了几年饭,有什么事理所当然都要互相照应,不然就太没情义了。”说着,像是想起了什么,从西装口袋里掏出名片夹来,很优雅地抽出一张递给于德祥,于德祥接过一看,上面印着一个什么公司董事的头衔,心里想,怪不得他出手这么阔绰,原来底岸蛮足。这时候醉眼惺忪的胡眯子也递过来一张名片,是镶边烫金的,有香味,比和尚的又要显得档次高出许多,上面的衔头是欧亚地板砖公司副总经理。
“你把生意做到欧洲去了?”于德祥将信将疑问。
“他的地板砖早和国际接轨了。”韩月球笑道。
“我那纯粹是撮汤锅子,来一个剁一个,牌子大得吓死人,其实就是二马路杂货铺楼上的一间破房子。”大家都笑。
于德祥又问了韩月球和杨卉芳的工作,原来韩月球下岗后应聘到一家家电公司做销售,经常在外面跑,销售业务加上底薪还有差旅费,收入还不错。杨卉芳因单位效益不好,今年辞了职,还不晓得做什么。
“你反正老倌赚得大,妹子又会读书,将来出国留洋,大把大把地赚美金,你还不如干脆在家里做全职太太得了。”韩月球朝杨卉芳说。杨卉芳的老倌自己开了家轮胎店,请了两个帮老倌,店子虽然不大,却当街,生意不错,她的独生女是音乐学院学钢琴的,听说还没毕业就已经有好几家琴行打算请她去当调琴师,所以韩月球常常说杨卉芳不用想事了。
牛呷禾草鸭呷谷,各人自有各人福。的确,人活着就得有“奔头”、有想法,这样活起来才有点意思,于德祥心里不由得掠过一丝悲哀。这顿饭吃了三个钟头,胡眯子才剔着牙花去联系汽车,他们打算绕过龙虎关然后直奔阳朔,都是50来岁的人了,又拖儿带女的,今后还能来得几趟?他们都想就便到阳朔去玩。其实,于德祥从没去过桂林和阳朔,当和尚和胡眯子一再邀请于德祥两口子一起到阳朔去玩时,于德祥又托辞不肯去,大家也便不再勉强了,离开江永时,于德祥一路跟着直到把他们送上车。汽车后面冒出几缕白烟后便擦着柏油路面往前直飙,好久了,于德祥还呆呆地站在那里……
牛崽的汽车进入市区后天已大明,轻纱似的薄雾渐渐褪去,做早市的餐饮店已经开门迎客了,车子绕过几道弯后便到了毛家桥,牛崽将车直接开进了货场。于德祥长长打了个哈欠,有些费力地从车上跳下来:“这是哪里?”
“于叔是老长沙了,怎么连毛家桥都不晓得?”牛崽拍拍一身尘土笑道。
毛家桥于德祥当然晓得,可是他毕竟又有20多年没回长沙了,怎么看这里都不像记忆中的毛家桥,看着于德祥左顾右盼的样子,牛崽便笑着问他打算先去哪里,于德祥本想说到南门口去找和尚,又怕牛崽笑话他不认得路,只好说先到姐姐家看看再说。
于德祥的父母早不在了,长沙只有一个姐姐,住在浏城桥下面的复兴街。原先在一家塑料厂做工,后来厂子垮了,一家人全靠姐夫王吉福替人修锁配钥匙维持生活。于德祥这些年很少跟姐姐联系,因为王吉福这人从来就把钱看得跟命一样要紧,以前就生怕老婆拿了家里的钱贴补娘屋里,两公婆经常为钱吵架。于德祥不想去姐姐家啰唣,心想要是找得到事做最好,先安顿下来后再抽空到姐姐家去看一下,饭都不想在那里吃,免得看王吉福那张拉长的马脸。
前面那个烟摊上有公用电话,于德祥下意识地翻了翻口袋,从里面摸出一札皱皱巴巴的名片来,他选出和尚的那张,按上面的号码拨通了,一会儿那头瓮声瓮气问找谁。“喂,朱老板吧,我是于德祥老于呀,才到的长沙……”话没说完,那头就不耐烦了,“什么猪老板狗老板,这里没有!”对方没等于德祥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于德祥只好耐着性子麻烦他找朱克强听电话,谁知对方操一口京片子阴阳怪气地说:“你到公安局去找吧!”说罢重重地将话筒挂了。于德祥顿时懵了:到公安局去找,能有好事吗?他不是好好地当着董事长,威风八面管着几十号人吗,为什么到公安局去了?于德祥当然知道公安局是什么地方,没有事能被请到那里去吗?他满腹狐疑地又翻出胡眯子的名片来,电话一拨就通,是胡眯子亲自接的,于德祥告诉他,自己才到的长沙,现在还没落脚点,又说刚才打电话给和尚,一个不认识的人要我到公安局去找,晓不得是什么意思。胡眯子说你不要去找和尚了,他已经进了笼子。得知于德祥来长沙的目的,有些为难地说这事还真有点不好办,然后告诉他下午见面时再谈,说了联系方法后就把话筒挂了。
于德祥提着沾有泥屑的合成革旅行袋,沿着湘江风光带一路走去,他想到姐姐住的复兴街去看看,又怕碰见了熟人告诉姐姐让她操心。这时候他才想起自己还没吃东西,听说城里好些个体餐饮店都很“黑”,自己穿得土气,一看就不像城里人,面前虽然有好几家面粉店,看样子都有些档次,于德祥却怕挨“剁”,再则也想省点钱,于是又回头折进一条小巷,找了家他认为适合自己身份的常德米粉店坐下,店老板好像也是农村人,男的挑粉,女的管收钱和收拾碗筷。见生意来了,都很热情。粉很快就煮好了,于德祥吃过后感觉不怎么样,价钱比江永的贵,份量却少多了,至于味道,吃惯了江永那种米线圆粉的于德祥也觉得好不到哪里去。从小粉店出来,于德祥一脸茫然地在街上乱串一气,长沙的变化太大了,于德祥有些分不清东南西北,尽管几乎一宿没合眼,还是觉得很兴奋,经过五一广场时,他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在他的印象中,五一广场正中是一幢大石碑,上面刻写的是当年那位红得发紫的副统帅的题词,整个广场显得沉闷而压抑,可如今,这里花木葱茏,棕榈碧翠,幽幽曲径令人神往。于德祥只觉得活了几十年,从没见过这般美景,他在一条考究的大理石长条椅上坐下来,眼睛在一伙玩滑板的小青年身上停住了。他忽然想起自己刚下放时也正是这般年纪,却比他们成熟许多,那时候的口号是要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尽管乳臭未干,大家都感到肩上担子很沉重,仿佛立马就要去赴汤蹈火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哪有闲工夫玩耍。
这时候太阳渐渐升起来了,照在身上暖和和的,于德祥看看手表还早,他想靠在石椅上打个盹,可是毫无睡意,干脆起身不紧不慢地踏着弯弯幽径浏览起这座市民广场来,就这样这里看看,那里走走,很快到了下午两点钟。他这才掏出名片来给胡眯子打电话,胡眯子问他现在在哪里,他张开口望了半天竟回答不出,只好问槟榔摊的胖子堂客,胖子堂客告诉他,你就说是新大中旁边好了。胡眯子叫他千万不要走开,他一会儿就来。果然还不到一餐饭工夫,胡眯子就来了,穿着黑色的隐纹西装,鼻梁上架着大蛤蟆镜,脚下皮鞋贼亮。
胡眯子领着于德祥拐进一条小街,来到一个名叫月亮船的小茶楼。刚一进去,就有一个年约三十来岁,头上盘着发髻的女子迎上来:“胡老板好久冇来了,咯向只怕老婆管得蛮紧吧。”胡眯子使劲一挥手:“去!去!该做什么做什么去,莫在咯里逗骚,老子今天有正经事。”
“哟—,真是,三天冇偷小菜,一下子正经起来了。”那女子撅着嘴说,便扭摆腰肢领着胡眯子往楼上走,一边走,一边将盘起的头发披散开来,一股劣质的洗发水气味直往于德祥鼻孔里钻。两人走进一间包厢,胡眯子冲外面一个女子喊声泡两杯绿茶,把热水壶放在里面,老子自己伺候自己。
茶水很快上来了,那女子又顺手将门带关。
“你说想来长沙寻点事做,是吗?不是我泼你的冷水,现在大街上闲逛的,起码有一半是下岗工人,像你这样一冇得背景靠山;二冇得文凭学历;三冇得一门过硬的技术,年纪又是咯号年纪,哪里好找事做啰。”于德祥一听木了,找不到事情做,我来长沙做什么?可他仍不甘心,忙问和尚到底出了什么事?“胡眯子望了一眼已经被带上的门:“还不是为钱,这贼胆子也忒大了,居然想乱税务局的砣,只顾在钱眼里打圈圈,冇想到早就有人绿眉绿眼盯上了他,自己栽了还不晓得绊在哪个手上。如今被关在乌山湖一个什么地方,上个礼拜我和刘胖子去看了他,这狗鸟的真的经得熬,三个月了还是膘肥肉满的,没落一点架。不过,你就是找到他也是空的,你想,他自己都关在笼子里,哪还有能力顾及别人。胡眯子说罢从口袋里拿出一包软白沙,抽出一支递给于德祥,于德祥接过那根皱巴巴的纸烟点燃,一头雾水地望着胡眯子。
“不过,你也不要着急,既来之则安之,好不容易回了趟长沙,总要给你想想办法,你现在住在哪里?”胡眯子问。
“我是搭拖柚子的便车过来的,还没找到住处。如果硬是找不到事做我还是坐便车回江永去算了。”于德祥满脸沮丧地说。他心里想到胡眯子办公的地方去看一下,当到副老总的人,总该会有些门路的,尽管他也晓得胡眯子牛皮哄哄的,但闯荡江湖这么久,他相信胡眯子朋友多,路子宽,也许能想得到办法。可胡眯子却没有邀他做客的意思。
于德祥在长沙瞎转了两天,晚上就和牛崽他们几个挤住在江边一家名叫“春来”的小旅馆里。这旅馆其实就是相连的两间居民住房,每间房里放了三张床,一张摇摇欲坠的桌上放一架14寸的黑白电视机,床上的被子仿佛隔了十几年没洗,发出一股刺鼻的霉味,于德祥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习惯。看来在长沙找事做是没指望了,他想到姐姐家去看一下,然后就跟牛崽的车回去。其实他昨天就到复兴街去过两回,复兴街到处是一幢幢摩天大楼,哪里还找得到原来的影子。印象中姐姐家的隔壁是一家炒货店,他来回寻了两次却找不到踪迹。正不知所措时,只见一个婆婆拄着拐杖从路边店里出来,于德祥忙赶上去问:“老娭母也,请问这里原来有个叫王吉福的老住户,你朗家晓得如今搬到哪里去了?”
那老婆婆就站住了,若有所思的样子,一会儿又问是做什么的。
“就在街口上摆了一个修锁配钥匙的小摊,也修拉练和手电筒。”老婆婆双手交叉叠放在拐杖把上,眯着浑浊的双眼上上下下打量于德祥。
“王吉福是我姐夫,我就是月娥的亲弟弟呀,一直下放在江永农村。”于德祥忙说。
老人“哦”了一声,“原来是咯样的,你真的是月娥的老弟?快莫提了,王吉福捅了人坐牢去了,你姐姐也早搬走了,听说搬到了桂花井那边,在那里开了间日杂店,我也好久没见到她了,你自己去找找看。”老人似乎对王吉福一家蛮了解,于德祥谢过了这位老人便径直往桂花井去了。
于德祥找到姐姐后暂时就住在她那里,他把姐姐家的电话告诉了牛崽。过了几天,牛崽又从江永拖了一车柚子过来,这是他今年最后一次来长沙,因此打电话告诉于德祥,问他是不是坐自己放空的车子回去,不然,以后回江永就只有买票坐客车了。电话是于德祥的姐姐接的,她先替于德祥谢了牛崽,说想留于德祥住些日子再回去。
牛崽的爹老子天旺老倌原来是大队会计,也是于德祥刚下放时在队上拜的师傅。牛崽是天旺老倌的满崽,于德祥招工到县城以后才出生的。于德祥当了工人后,不几年又讨了老婆,牛崽那时在县城中学读书,常在于德祥家歇宿,后来他参军了,在部队学了汽车驾驶,几年后又转业回了江永,年纪轻轻的他可不愿像老班子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翻一辈子泥片子。一家人东挪西借,又找信用社贷了款才买了这辆东风大卡跑起了运输,他跑长沙已有一年多了,以前也曾多次邀于德祥坐自己的便车回长沙看看,可于德祥一直提不起兴趣,爹娘都不在了,再说自己混成这个样子,回长沙去有什么意思。如今这世道只认得钱,有钱就是大爷,没钱就只能装孙子。他不想让长沙的亲戚熟人看不起自己,他觉得自己和长沙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