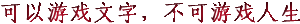家 有 仙 妻
听说台湾(还是新加坡?)有个电视连续剧叫《家有仙妻》,我没有看过,不知道那位仙妻是如何个“仙”法,但我却要借这个剧名用在自己身上,并非我妻子容貌非凡,更不是她神通广大,而是她平日里常有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谈举止,朋友说她是“云里雾里放光彩”。(湘北一带用“云里雾里”形容糊涂)你说,若不是“仙”,能云里雾里放光彩吗?
要说我那位“仙妻”,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我们是怎样成为夫妻的。
湘资两水相抱的大垸内有个鹅湖,鹅湖有条泻洪沟,沟北是我当知青落户的生产队,沟南是她落户的生产队。她和我都是年幼丧父,跟随被发配到乡村小学任教的母亲以校为家;母亲都在文革中首当其“革”,她母亲含冤而故,我母亲被遣送改造;同队知青都已陆续招工回城,我和她都因为政治原罪而回城无望,逢年过节也无家可归。不过,两人都认命,懒得怨天尤人,打算就在鹅湖之畔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听一辈子风声水声。然而,讨嫌的是两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提亲做媒的简直象如今上门推销菜刀的那样烦人。她那边不但老兄介绍了同厂的工人老大哥,,住户嫂子介绍的三位贫农哥哥也已分别登门相亲。我这边队长的老娘介绍了两个让我倒插门的对象,只是一个双足长短不一,一个已经二度梅开。老太太说:“你如今吃的在口里,穿的在身上,屋都没一间,阶级又大,只能将就点……”
一九七二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独自一人荡着小船在鹅湖摘菱角,与她不期而遇。我邀她上船,各自说起了自己走桃花运的故事,两个人都笑出了好多眼泪。笑过之后,四目对视,同时想到了“同类项合并”这个解题法则,只是当时谁也没有说出来。但从那以后,只要月朗星稀,我和她都会鬼使神差般地在鹅湖边相遇,要么是一叶扁舟荡漾湖中,唱着拉兹和丽达的歌;要么是坐在湖边看波光粼粼,听蛙声阵阵。不到半年,两只飞不起的孤雁终于依偎到一起。
接下来,我在社员们的帮助下用土砖砌了两间茅屋、垒了一个灶台,用刚学了两个月的木匠手艺做了一张床,再将她的炊具和行李搬了过来。然后,我们走到公社,掏尽荷包凑起一元八角六分钞票,买了一包大红花香烟和一捧水果糖分发给在场的同志,领取了结婚证。接着,我们向生产队请假回家举行婚礼。其实我们都无家可归,只是在邻近公社的知青点转了两天,回到新砌的小茅屋后,她就成了我的妻子。
从谎称回家举行婚礼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这三十五年间,我们在鹅湖边生活了四年,转点到一个农场生活了三年,七九年知青大返诚才同时招到县城,后来调到岳阳,再后来调回长沙,如今都成了退休老人。三十五年,白云苍狗,我们所处的环境一变再变,但她始终依然故我。现在孙子都三岁了,她这位奶奶还时不时地“云里雾里放光彩”。
刚住进鹅湖边新茅屋的时候,我们连饭桌也没有。她捡回一个穿了底的箩筐倒扣在地,上面放个小米筛充当饭桌。碰上县知青办的干部来调查,她说:“出身地主嘛,当然是筛罗(锣)吃饭哟!”(过去大地主家里长工短工多,有的用敲锣通知开饭,鹅湖一带将“敲锣”说成“筛锣”)县里干部听了这话表情严肃,而我这做丈夫的只能报以苦笑。听说我们成了家,一帮知青朋友前来祝贺,我们能用于招待的仅有一锅米饭和一坛红辣椒,但大家吃得很开心,一双双筷子竟相伸向那半脸盆红辣椒。她说:“这才真正是个个向往红太阳。”
她不但想到什么说什么,口无遮拦;而且想到什么做什么,不顾其他。当年双抢,我出早工她做早饭。有天我回家吃饭,饭还没煮。她不是起得迟,而是进园摘菜时见菜地要除草施肥,便忙着舞弄起菜地来,把煮早饭忘到爪洼国去了。乡下蚊子多、老鼠多。床铺草上有谷壳,惹来老鼠将蚊帐咬出个大洞。双抢紧张,白天没时间补,到了晚上她急中生智,操起剪刀将蚊帐齐鼠洞剪去一截,然后再将蚊帐吊矮一截。我双手合十求菩萨,祈求保佑蚊帐莫再遭鼠咬,要是再咬再剪,蚊帐就会矮得钻不进人。她恍然大悟,笑得前腑后仰。
有一次,不记得我是犯了什么错激怒了她,她板着脸命令我:“今天硬要跟你吵一架,你不准又用玩笑扯开!”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三十六计走为上,不料她穷追不舍,边追边喊:“我是真要吵咧!你要跟我吵呀!”惹得好多人出来看热闹。但我终究逃脱了追兵,在别人家吃了晚饭才回去。满以为她那里箭拔弩张等君入瓮,殊不知她已被《北极风景画》的手抄本所征服,早把要吵架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
她是小说迷,契诃夫、泰戈尔和莎士比亚,琼瑶、三毛和金庸都是她的最爱。她也是电视迷,百十集的《女奴》、《卞卡》和现如今的韩剧,她都不会错过一集,而且陪哭陪笑。每当进入情节之后,她的脑袋就会刀枪不入。在县城时,有位乡党委书记来家里坐,我给正在看书的她介绍:这位是某乡的李书记。她起身打招呼:“柳书记好!”待我纠正她后,她泡茶递上:“刘书记请喝茶!”待我再笑着纠正时,她已重新捧上书。到李起身告辞时,我拉她送客,谁知她又蹦出一句“周书记走好”。为了掩饰她的云里雾里,我笑着骂她:“你真没名堂,初次见面就玩笑开个不完。”李书记急忙解围说:“嫂夫人是乐天派!”
她就是这样一个不上心的人,出门忘记带钥匙、存折忘记密码、买了东西忘记拿、去过多次的地方走错路、微波炉里的菜忘记端、电饭煲下了米忘记按开关……这些都是常有的事。更尴尬的是,有两次到朋友家送红包喝喜酒,一次是出了门才记起红包还揣在自己蔸里;还有一次是红包里忘了放钱,人家帮忙收礼的对不了帐只得找上门来询问。
不过话说回来,只要是她上了心的事,是绝对不需要别人操心的。我母亲在世时爱看古装戏,我们不爱看,但只要剧院有这类戏上演,她都会买好票送老人家进剧场坐好,戏散后再准时去接。在县城时,常有鹅湖的农民朋友来县医院治病,或者过年过节来家里作客。她都会帮住院的送去煤炉炊具热水瓶,给来家作客的回赠礼物。那时候每到过年,她都事先买回一段段的确卡和毛哔叽准备着。再就是每年七月半,她都会及时筹办好冥钱香烛,为已故的亲人烧包,而且每年都会让三位已经作古的孤人享受同等待遇,一位是她母亲的同事、一位是我的忘年交、还一位是我的初中同学。
她爱唱歌,在家里常常歌不离口,做饭唱,洗澡唱,有时晚上十一二点也会来上一两句,邻居说我家常演“夜半歌声”。她还喜欢郊游,钟情于青山绿水。她每去一次乡下都会满载而归,全是自己采摘的映山红、蕨、车前草、田边菊之类的野花野草。每当玩得兴起,她就会有笑话爆料。前不久去骑马,她右脚蹬上了左边马鞍,左脚跨不过马背去,忙喊儿子帮忙:“我前脚上来了,后脚上不去。”儿子笑她:“妈妈不属马呀,怎么左右脚变成前后脚了?”她发现自己口误,笑得差点摔下马来。
她爱干净,要是发现有一丁点异味,立马要清剿。毛巾隔三差五要用肥皂水煮沸一次,至于被小说或电视所害,煮焦了多少毛巾则不得而知。可她又不爱叠被子,起床后将被子翻个边了事。她还说如果家里收拾得象宾馆一样规范,就会少几分温馨浪漫。她的衣柜也常常整理无序,有时一开柜门就有衣服随之滚落出来。但她上班做事又一丝不苟,比方她整理的档案就能与精装书比美。要是我和儿子说错了什么,她会当即指出,但换了同事和朋友,哪怕明知是在玩乖巧、使心计,她都会云里雾里,反应迟钝。我怪她“里外有别”,她说:“能糊涂时不糊涂,就等于跟自己过不去。”
在保健养生方面,我们分歧很大。她信奉猴论,好动不好静。而我主张乌龟哲学,好静而懒动,猴龟两论之争便成了我们的主要矛盾。她经常变换战术来征服我,不是在我上网时施加歌声干扰,就是指使儿子孙子拖我外出散步,有时还要朋友出面邀我去爬山逛公园,甚至请来医师朋友把不锻练的后果讲得危言耸听。不过,我对付她的招数比这些更损。记得在县城住通走廊宿舍时,她批评我下了班既不做家务又不做运动,是机关院内头号懒鬼。我便拿起她一条花短裤打上肥皂,从走廊东头搓到西头,无话搭话地让邻居们都知道我在为老婆洗短裤。第二天,妻子成了机关家属们羡慕的对象,我成了全机关最勤快的男人,她则有口难辩,有屈难鸣。虽然类似的恶作剧也还有过,但她知道我是秉性难改,并非恶意伤她。再说,一旦出现真有可能使她伤心的情况,我都会采取紧急措施。大前年她在岳阳治疗血吸虫病一个月,我因公事缠身一直不能去看她,她回家那天我也没去接。但她一打开门,就有一连串的鲜花从一楼摆上二楼,直摆到她的床上,还插有不少道歉和祝福的卡片。当我下班回家时,她热泪容眶地吻了我。
我名字中的后一个字是“平”,她的是“安”,加起来是“平安”,可能这就是缘份吧。正因为有这个缘份,我才敢对她公开挑衅:“你样样比不上我,只是你找的对象比我找的对象强”。她也不恼不气,因为她知道我为有她这位“仙妻”而感到幸福快乐。这些年流行过西方的情人节,我也被聊发少年狂,每逢情人节都给她送玫瑰。但去年记错了日子,情人节当晚小儿子幸灾乐祸地问我今天是什么节时,花店早已关门。我就再一次采取紧急措施,用宣纸写了四句平仄不当的歪诗代替了玫瑰。诗曰:“险道泥泞共搀扶/艰辛酸楚两心知/今生相伴慢慢老/来世再为连理枝”。不料她居然拿去画店作了装裱,挂在了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