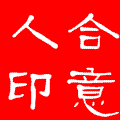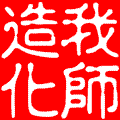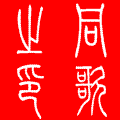往亊锁记之囫囵呑下三头猪
耒阳与安乡地理环境差异很大,物产也不尽相同。若要论个好坏,我可不敢在安知网站较真,因为这里的网民大多将安乡视为第二故乡。世上又有几人不说自己的家乡最美呢!但心平气和单论地貌,丘陵地区的耒阳与长江泥沙冲积而成的安乡,在层次上是要丰富些。我下放的那个大队,三面环绕着耒水,一般情况下耒水河平静、清澈见底。高高的河岸边是砂质土壤,套种着花生、棉花、芝麻和高粱。离岸稍远一直到我们居住的那幢大房子,中间是沟渠纵横旱涝保收的良田,稻田的灌溉,不直接取耒水河的水,依靠干渠从远处深山中的水庫引出。大房子的正门 外,有一大块平整的场地,是小孩们玩耍,大人们聊天的好去处。场地边有几棵先人种下的古樟树,都有展开双臂合抱不下的树径,树冠似华盖。古樟树下有一口青石砌就、旱季不涸、雨天不溢的水井,无论冬夏那井里的水都带着丝丝甜味。过水井下坡,不多远是大水塘,围绕着水塘的是村民、也包括知青的自留菜地。大房子后面是成熟的坡土,大面积种着金钟(俗称黄花菜)。翻过种植黄花菜的山包又是水田,不过,这些水田似乎像后开发的,整齐划一。再往远处走便是油茶树林和其它用材林了,林间空隙坡地点种着红薯、荞麦。这如诗如画般美丽的田园就是我抛洒了三年青春汗水,养育了我三年,至今仍令我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如果非要指出缺陷,那就是我们大队山多田少,大概是7与3之比,人均粮食占有量那是远比不上安乡了。红薯等杂粮要当半年的家。当地有句戏谑话“三碗红薯饭尽饱”,这是在语言上玩了个时间差的小把戏,试想三海碗红薯下肚后,还吃得几多饭。
第一年国家拨付了安置费,大队保证毎个知青36斤米一月,没觉得吃饭有什么问题,倒是觉得耒阳物产丰富。烧的是本县自产,从水路运来、价格低廉烧得起的优质白煤,每家都有一个灶膛直径不小于12公分的地灶,煮饭、烧水都在这里,冬天其取暖效果决不比空调差,一年烧三个季度地灶。夏季、炒菜则用堂屋里的柴灶,燃料多的是,稻草、茶籽壳、从山上扒回来的干树叶、枯树枝。油也是有得吃的,队上经常分茶油、花生油、棉籽油、菜耔油。除炒菜外,我们还油炸了些红薯片、糯米糕当点心吃。这并不像特艰苦的生活。确实。考验是从下乡满周年后的第一天开始。我真正羡慕下乡几个月就被招工回城的知友,他们是命运的宠儿,可惜我们大队没有一个。
第二年知青与村民享受同等的待遇,每人30斤谷一月。村民家老小多的,扯平了吃,再辅以杂粮、蔬菜尚可糊口,差强渡日。家里青壮年劳力多的,过日子就艰难了。知青们基本都处在青春发育期,30斤谷无论如何维持不下一个月的生计。减少了粮食,一切生活程序均被打乱,开始时,我们往米汤中加入削成大块的红薯熬稀饭,很快发现红薯消耗太快,不到播种育秧时就没有了。我们也学习村民,拿钱到灶市(地名)买红薯渣饼。所谓红薯渣饼,是做红薯粉的下脚料。鲜红薯磨碎,经细布滤出淀粉后留在布里的渣,用手捏成饼状粘在墙上,自然风干。逢赶集的日子,有人一担担挑着在集市上卖,买的人大多是渡春荒的农民。这东西煮在米汤里并不难吃,照现在的营养学说,应该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减少体内脂肪沉积很有帮助。我们那可怜的肠胃本就没有什么可沉积的,随着红薯渣饼煮米汤下肚,越吃越饿、饿得心慌。可是这样的日子也继续不下去,临近早稻扬花时,有钱也买不到红薯渣饼了。我们曾试着往米汤里加最细的米糠做的圆子,但米糠没有粘性,一煮就散了,实在无法下咽,只得忍痛倒给邻家喂猪。之后我们就早晚米汤、中午干饭的下田、活着。米终究快没有了,我们向生产队反映了没饭吃的情况,可能大家都如此,两三天还没有回音。那天晚上,我们三个知青喝完了最后一餐米汤,早早地躺在床上,终于有一个同学耐不住寂寞,跟我们侃起回家过春节,吃大碗红烧肉的故事。我的神经系统很快有了反映,口腔里充盈了唾液。随着她大侃特侃红烧肉的美味,我仿佛独自走出了家门,走啊走,我来到一栋猪舍不象猪舍、餐厅不象餐厅的建筑物前并随手捡起了一根竹棍,迈进大门一看,哇噻!好多猪呀。这猪能走能动,但怎么看都象红烧过的。一头猪来到我面前,我毫不犹豫用手中的竹棍将猪往嘴里一赶,胃里面果然好受些。第二头猪来到了面前,依前法第二头猪又进了口,可能是吞得太猛,咽喉有被卡住的感觉。这时第三头猪也来到面前,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吃个饱,我将第三头猪也赶进了嘴。果然吃得太多、要吐了。哇地一声睁眼一看,哪有什么猪舍、餐厅、红烧猪,我的嘴里塞满了被子,这被子的一角已经浸透了口水。扯出嘴里的被子,眼泪哗哗直往下流,同伴们的床上寂静无声,我不敢哭出来,听任眼泪染湿了被子的另一角。想到已经粒米无存、离发口粮还有些日子,一股冷气从骨子里往外窜,我倦缩在被子里,越团越紧,终于昏沉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似乎听得有人喊:学生妹子,起床挑谷去。不是又在做梦吧?起身一看,屋里的同伴都在穿衣,门外确实是队长黄显生在喊叫,我穿衣下床,此时黄队长已经手握锄头进了屋。他看到我们的地灶没开火,鼎锅里只有水,自言自语道:果然是没有米下锅。便吩咐某某去喊保管员、某某准备箩筐、扁担,真的带我们从装种谷的仓库里挑回了90斤稻谷。这位黄显生队长,从小是个孤儿,青年时被抓壮丁,在战场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没有什么文化,但为人公正敢于挑担子,知青们这次没饭吃了,他居然说出:饿坏了城里来的学生妹子,是政治问题。谁敢负责!种谷也要让她们挑。这超级水平的话,使生产队的领导们一致同意给我们多发一个月的粮食。依靠多发的粮食和不久后发下来的口粮,我们渡过了春荒,终于迎来了双抢。
双抢中,我干的是跺灰印的轻松活,这大家已经知道。我为每天两餐干饭、晚饭可干可稀的待遇欢欣鼓舞,跺灰印和次日检验灰印时,我不仅仅是兢兢业业,简直有点如履薄冰、胆颤心惊。因为我不是从语言上和书本中知道粮食的重要性。而是亲身体验到粮食就是生命的组成部份。
早两年乡下来人说:现在山里的物产运到衡阳、广州都能卖个好价。我们下乡时住的那幢大房子和其它住房,按照村里的统一规划都搬迁到了用材林的那座山上。老房子的宅基地都开发成了水田,水田的面积扩大了一倍。钱有了,粮食也有了。可惜忘记问那几棵古樟树和水井的命运,祈盼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