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曾经的年代 作者:英夫斯基(安乡知青)
----写在俄罗斯年
(1)
在我们曾经的年代里,有着太多深深浅浅的记忆,尽管我们想遗忘的想留下的都有种种理由,但在我的记忆里总有一段想忘也忘不了想留又不敢触动的岁月。时间过去了一个十年,两个十年,三个十年……还在不断往后延续。每过去一天都好象在往这往事的土堆上再加一杯土。以为没有了,永远的消失了。但潜意识里知道,尘封的记忆毕竟没有死去,它一定还静静地躺在心底的某一个角落里,它在等候哪一个时刻的来临?
05年初,网上偶遇一位聊友,可能对我这名字有点好奇,从我明显有俄罗斯味的网名上很自然地切入到前苏联的话题。他谈鲍罗丁,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他谈托尔斯泰,西蒙诺夫,甚至阿赫玛托娃,他还谈邦达辽夫,日丹诺夫,华西列夫斯基……一个还不能算中年的人居然把属于我们那代人的东西谈了个透。随着话题的深入,慢慢地,我知道,那个蛰伏了多年的时候来到了。记忆之门开启了,就像刚刚苏醒的睡美人,重新找回了沉睡百年的那个世界。
那是一个光明灿烂的年代,一个50年代所有的学生和青年们共有的年代,包括十多年后被称作知识青年的我们。那时正值苏联主导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解放了半个地球不久,正在进行着拯救全人类的伟大实践。我国的新制度刚刚建立,也正在老大哥的帮助下向共产主义迈进。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啊,没有吸毒,没有贪腐,没有不公,金色的太阳,透明的空气,水晶般的世界。全民高唱中苏友好,苏联的红色影响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建设全面覆盖中国大地。那时我应该是从幼儿园毕业的年龄,记得幼儿园教室里挂着一个爷爷的大照片,上唇长着胡子,穿着带领章的黄绿军装,老师说那是斯大林,还有一个老伯伯不穿黄军装(因为没长胡子,我坚决认为不是爷爷),一件海蓝色外衣的大翻领上缀着金色的饰纹,老师说那是伏罗希洛夫。从小看到的是苏联领袖的头像,是镰刀和斧头图案,听到的是“嘿拉拉拉嘿拉拉拉,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苏人民大团结打垮了。。狼呀(打垮了谁啊?歌词忘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小就知道中苏大团结)。走在街上,我也常常被苏联的老伯伯抱起来,他们又高又胖,在我一个孩童眼里就是一座小山丘,开始坐在他们肩上时,真的好害怕,第一次离地那么远,后来习惯了,倒不讨厌这种遭遇了,那么近地看着他们那些亮得透明的灰眼睛,蓝眼睛,让我想起我的万花筒,觉得又进到了那个五彩世界。
我的童年,就是与苏联连在一起的,我习惯了那个有苏联印迹的年代。
上小学了,我们学校想来应该相当于现在的中苏友好实验小学。常常上着课,就进来一行
也还记得我小学四年级转学回长沙前,大队部存放的众多苏式纪念品中的一尊少先队队鼓。那是由我们班班长代表学校亲手从一个满脸笑意的苏联校长老爷爷手上接过来的,当手交手的那一刻,队鼓齐鸣,那沙沙的鼓点声和着我们踏步的整齐节奏敲得我们心花怒放。
这就是一棵小苗的生长环境,给一滴雨它就湿润。我就象一块干涸的海绵,拼足了命的吸干每一寸空气中的水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让小小的心灵激动得无法自控。乌里杨诺夫从小敢于承认花瓶是自己打碎的勇气成了我们永恒的榜样。我甚至会唱很多首我那个年龄不可能理解其义的爱情歌曲。记得比我大十来岁的小姨妈教我唱了一首顿河哥萨克杀死自己妻子的歌,至于为什么要杀死她我到今天也没搞明白。只记得那歌中有一段是妻子哀求她的哥萨克丈夫到夜深人静时再杀她。歌词现在是不记得了,但那哀婉的旋律很打动人,所以遇到我的大人都拦着让我唱给他们听,不唱不让走。常常被堵在厕所里给人唱,以至于我都不敢一个人去上厕所。我还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唱“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我和我的爱人上战场”,唱卡秋莎,那位小伙们喜欢的明媚的苏联姑娘…….唱起来全然没有一丝羞涩。在那个七情六欲还没发育的阶段,我心目中的爱人决不是具有雄性特征的具象的“人“,勇敢炽热深沉豪放富于牺牲精神,这才是陪伴我们那代人一生的爱人。
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歌不唱了,也听不到了。镰刀和斧头也不见了。就像我每天必定经过的小道两旁的老树,天天从它下面经过,也没留意哪天起它满树的叶子就掉光了。这时,我也惭惭懂事了。好像是上了中学了吧?可能是60年代初吧,中共九评发表了,我还并不能理解它的实质意义,隐约觉得与苏联有点不对付了,但并没想过这对我意味什么。紧接着赵朴初的那首《哭三尼》见了报,好像全国人民都很振奋。我也很懵懂地高兴,很得意地用标准的普通话把它念了个字正腔圆,还一次次地修正卷得不到位的舌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情景于我与阿Q临死前于那个最后的圈画得是否圆一样,十足地具有悲剧性。
那时只要是沾了苏联的边的东西,不论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是真实是谎言,是精准是偏颇,都会发自内心的关注和兴奋。为他的共产主义兴奋,为他变成修正主义兴奋,为赞美他兴奋,为咒骂他兴奋,为中苏友谊兴奋,为中苏破裂同样兴奋,没理由的,一概兴奋。反正苏联是个神经结,只要触到它,兴奋不已!!! 一个有头无脑的时代造就了一个有头无脑的我。
(2)
时间又往前走了好多年,这时的我和我们遇到了更出奇更没法按常规理解的事件,我们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一直不理解,怎么一个绞杀文化的革命会以文化给自己冠名?) 文革开始的日子里,从觉得新奇到趁机玩个够再到惊魂不定,这时间进程并不算太长。没多久,从对黑七类的抄家行动很快转为派性斗争,我也从恐惧和高压下稍稍回归了平静。当家长们该抓的已抓该斗的在斗,各派组织该保皇的在保皇该造反的在造反的时候,我和我们大院里各种年龄的孩子们也在这暴风雨的间隙里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一群我弟弟那样大的孩子到离我们大院不远的省图书馆偷了一大批书,当时我看到那堆书时吓了个半死。我弟弟却很潇洒的说(借用了这个几十年后才被广泛运用的词,觉得很应当时弟弟的神态),怕什么怕,图书馆早就没人管了,连看大门的人也没有。你们还要不要我们再去拿些回来?再不去就都被别人抱走了。他们管这叫“拿”!想到孔乙已,觉得他们“拿”得也不算错,“革命无罪,偷书有理”,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嘛,于是我释然。按照我们大孩子开的书单他们又多次潜入了省图书馆。现在看来,不仅要谢谢苏联,也得谢谢那帮小兄弟,没有他们,我怎么能走进俄罗斯那座辉煌恢宏的精神圣殿,神游那片辽远广袤的土地,领略其民族深沉忧郁悲天悯人的高贵气质啊!
文革中的那段日子真绝了。在十亿人民走出厨房走出课堂走出工厂走出机关,在历史的舞台上为了“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这群无路可走的“可教育子女”都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通宵达旦,大饱眼福。苏联的旧俄的,美国法国英国的,印度希腊西班牙的,不知什么国家的,看了个昏天黑地,同样忙得眼圈发黑。那时内外世界居然如此相映成趣:屋外在哗啦啦的改天换地,屋里在静悄悄地脱胎换骨,各忙各的,两不耽误。但遗憾的是前者的改天换地也没怎么成功,而后者倒可能真的脱胎换骨了。
后来那些书随着院子里的人下乡下干校不知所终。不过也从没有人宣布过对它们的占有,它们总处在流动中,供所有人各取所需。我至今还很感叹:原来这种人类最高最理想的按需分配的分配形式,其实就存在于纯洁的孩子们中间,它原来离我们那么近,它本来就是人类的原生状态。倒是后来被现代文明破坏之后又费尽心机地号召人们把它再找回来---自扰的人啊。 哦,那些想起就叫人温暖的书!至今还记得那些封面,那些插图,那些被不知名的阅读者划了好些红杠杠蓝杠杠的书页……(尽管我最讨厌这种阅读方式),它们现在流落何方呢?它们曾经到底拯救过多少年轻的灵魂呢?它们知道40年后还有老友在这儿挂念着它们吗?
我的读书经历就是我的心灵回归史。许多许多年后当我真正具有了宗教意识时我首先感恩上帝的是我也许比同龄人更早地找到心灵的归属。归属感可能是造物主赋予受造物的共同特质,万物都不可逃避。你只要看看江河小溪,它们也在乎自己的归属,否则它们怎么总不肯停留一个劲向终点跑呢?近来常有“放逐心灵”诸如此类的说法,看到这类命题,我总颇感庆幸:我的心灵倒是早早就找到了精神家园。
那时的阅读量特大,我们都很乐意地把我们曾经深恶痛绝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再次用在自己身上。那时期各种题材体裁各种主义各种背景场景各等人物各种流派风格都在眼前大交锋大碰撞,火花不断地迸射出来。我日日夜夜被恐怖哀伤愤怒感动兴奋。。。。一切人类的情感搅得不能平静。但分明总有一缕光亮在前方照耀,总有一种情感在主导指引提升着我。它把我从西方文学作品中那些贪婪,孤独,冷漠,放荡,堕落,死亡,变态的漩涡里打捞出来。那就是充满激情理想又充满人文忧郁的苏俄文学。美丽的苏俄文学,她表现的不是人类的悲观消极和肮脏,她代表的是人性中最光明灿烂的情感。她阳光四射,纯洁芬芳,她庄严肃穆,崇高理想,像一座心灵的教堂。
当你看到聂赫留朵夫的道德忏悔一直伴随着玛丝洛娃的流放生涯时,你知道你看到的决不会是一个浪花子回头的老套故事,那种感情决不会只发自“同情”。那是“怜悯”!有人曾给“怜悯”下过这样一种定义:怜悯不等于同情,怜悯是愿意与被同情者一同受苦,是一种比同情更高更深刻的情怀。怜悯不仅仅要让弱者得到公正,它更在乎追问不公的根源,敢于一直追到自己的灵魂里去!它的延伸是良心的自我拷问。当你窥视聂赫留朵夫的灵魂,你会感到一股静水深流的强力冲击,感到神性对人的冥冥呼召。渐渐地你会产生“移位”的错觉,不由自主地转而直视自己的灵魂。也许从那时始,这种神性也开始在我的心灵里萌动。
在凛凛寒风中,被沙皇流放去冰天雪地的西北利亚的十二月党人,他们的妻子长跪于丈夫的脚前,深情地吻着丈夫冰冷的脚镣。这感天动地的一吻啊,我的心滴出的血也仿佛在那一刻凝固。当妻子追随丈夫的流放之地,她们背后是奢豪优雅的贵族家园,前面是荒蛮严寒的无边冻土,面对她们你能不感到灵魂的震颤吗?许多年后我看到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大道》这幅油画时,面对占据整幅画面的那条通往西伯利亚的车辙斑斑的流放之路,我还仿佛看到路的尽头那些注定一去无回的十二月党人,我的心一阵抽搐,再次体味到当年那群贵族革命者对祖国前途深切忧虑的悲凉情怀。
我也曾模糊地了解并很倾心民粹派这个词及它启示给我的美好意境,它给我提供了传统教育以外的另一个同样美丽的世界,在那里革命并非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革命是他们要为之献身的一种理想和恋情,有后来人说,他们怀着的是基督般的无私的爱。(后来人还说那只是一个乌托邦。当然是,也许是。因为从地缘学上是找不到乌托邦这个名称的,但是从地缘学上能找到天堂这个名称吗?但你能肯定真的没有天堂吗?)当时隐约感觉这种普世的爱与我们接触过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下层人的同情有很大区别,中国古士人多是居高临下的感情恩赐,从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哀声中我听到更多的是对自己不平遭遇的哀叹和由已才及彼的同情。在苏俄作品中我找不到这种自悲自怜,施爱是因为爱就是心灵的本质,不能不爱。这种博大的没有任何利益性的爱更让我为之动情。也许这正契合了我们当时太缺少而更渴望得到的人的尊严人的平等人们的相爱而不是天天沉重疲劳的“文斗武斗”的心情?
也曾经记得列宁批评过某位异化了的革命先驱(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他钟爱的是自己的革命理论而非实践,他因为不愿意看到自已心爱的理论在实践中破灭而走上背离革命的道路(大意)。当时我倒很欣赏这种离经叛道的单纯可爱,一种对主义本身的迷恋使他们更像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主义不是他们挥舞的大棒和工具,也不是操作手册,我宁愿看成是他们对理想的描述和情感的表达。最为可贵的是在苏俄各历史阶段中,这群持各种革命主张的革命者们,全都满心喜悦的投身其中去寻找和享受苦难。这种彻底的人文情怀整整激动了我的一生。在我眼中他们就是那群翻飞在暴风雨中的黑色海燕。其实那只海燕完全可以与海鸭们一同躲到岩石下,但它们却冲浪于电闪雷鸣惊涛骇浪去追求更高的审美境界。我相信这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极富感染力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也曾经为屠格涅夫优美的文笔所倾倒,美丽的俄罗斯田野似乎就呈现在你眼前,你闻到黑土地的潮呼呼的气味,你真切看到满原野淡淡的小花在高天下摇曳,你满耳都是白桦林里树叶对风的絮絮声……一切都渗透大自然的生命之美。是画?是诗?是音乐? 就是这片美得让人迷醉的土地,几十年来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每每心力交瘁时,在那片无垠的青青草地上仰面一躺,顿时会让我神清气爽!
也曾经从契可夫的《带阁楼的房子》中懂得了什么是好教养,从那时就学会了怎么样不让别人陷入难堪。那句“有教养的人并不是不会弄翻果酱瓶,而是在别人打翻果酱瓶弄污了桌布时不要去注意它”(大意),这不仅让我记了一辈子,甚至日后还成了我的“妈妈教材”。也懂得了什么叫优雅和美丽,以至于太重视追求内心的审美而导致日后与社会情趣总有格格不入,恐怕因此还错失了世俗人生的些许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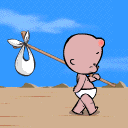

 ),加精了。如此看来,不是此文无知音,而是曾经的转发者人微言轻,无法引起关注。我明白了,也感到释然,不然还总觉得对不住好友,埋没了她的一番心血。
),加精了。如此看来,不是此文无知音,而是曾经的转发者人微言轻,无法引起关注。我明白了,也感到释然,不然还总觉得对不住好友,埋没了她的一番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