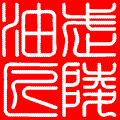倒霉后的幸运
昨天很倒霉,车在路上出了故障,但又在不幸之中遇万幸,享受到了三拨陌生人赐予的温暖。事情是这样的---
家住汨罗白水镇的堂叔昨天八十大寿,我携妻一同驱车前往庆贺。去是走的湘长高等级公路,宽宽的柏油路面无遮无拦,到湘阴后向东拐入省道湘李公路,在平坦的水泥路面再跑一十五公里,总共个半小时便到了目的地。一路上,太阳躲在云层里,风清气爽,景致如画,加上妻子一首接一首地唱着抒情歌曲,显得极为轻松愉快。
下午四点出发返回时,告别主人开出两百米,突然天降大雨,想起同桌客人中有位七十三岁的长者家住高坊,老人家回去肯定困难,便踩住刹车和妻子商量:我们走高坊到桥驿再转湘长路,虽然要走几十公里乡村公路,但可顺便将那位老人送回去。妻欣然赞同,我便掉转车头接上老人,驶入了乡村公路。从白水到高坊的公路都由水泥卵石铺就,路面不宽,会车超车稍难,车速受到限制。更伤神的是风雨之中,路上时有雨衣裹身的摩托车手和一手撑伞一手握把的骑单车者出没,必须格外留意,我只得开着防雾灯以四十码的速度谨慎行驶。到了高坊,老人千恩万谢地下了车,我们继续向前,挡风玻璃上雨刮器的摆动越来越快。
过了高坊不到三公里,雨小了,但车轮下变成沙石路面,车子颠簸起来。再走过不到一公里,碰上路面施工,两车道的路面只剩下百分之四十可跑,其余一多半正在铺水泥,车辆只能分段放行。耐着性子等对面过来十多辆车后,我们这头聚集的十来辆车才鱼贯而进。我排在这个批次的最后,前面是辆东风牌大卡车,右边是高出二十多公分的新水泥路面,槽型的钢铁模板还未全部拆卸,有的已被车碰翻在路边未来得及搬走。突然,前面卡车将一块扑着的铁模板压得翻了个身,我当即踩刹车,但右前轮已撞上U型模板的一角,随即发出了一声沉闷的爆胎声……
开车四五年,我这宝来从没发生过故障,自已连轮胎也没换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我的心猛地紧缩了,慌忙掀开后箱盖拿出千斤顶塞到车下摇起来。这时,身边不知何时蹲下一位四十开外的汉子,尚未开口,先伸手拨开我,抢过千斤顶摇手,这才向我发话:“你冒换过胎吧?去把套筒扳手拿来。”我顺从地按照他用长沙口音发出的指令站起身,从车后箱取出套筒扳手递过去,嘴里不由自主地嗫嚅着“谢谢、谢谢”。“那个保险螺丝呢?”我又转身向后,发现又上来三个中年男子,抬眼一望,我刚才等待放行的路段已停了四五台车,这几位肯定是那些车的驾驶员了。我这才记得掏出烟来,努力挤出笑容向每人递上一支。这四位没等我发出请求,便都动起手来。顷刻之间,烂胎被卸下、备胎被取出,接着烂胎被放进后箱,备胎被安装到位。可当我第二次掏烟时,只听得一个汩罗口音说道:“不行,右边球头拉杆弯了,开不得。”我急步走到车前头一看,发现新上的右前轮是正的,而左前轮却朝左偏出了三十来度。我刚刚舒展的心顿时又缩紧了……
雨又开始变大,两头的车在陆续增多,我的车卡在中间不能开动。在我一筹莫展之时,四位被淋湿的司机已经作出了决定,一个武汉口音指挥我:“你上车掌握方向,我们把车推到前面屋边上去。”另一个高坊口音却自已坐进了驾驶室并提醒我:“你去看看地上冒落下东西啵。”刚才取工具,事先将后厢内堂叔家送的鸡、蛋和蔬菜都搬到了路边,我顺从地向后走去,未见拉下任何物件,回头时车已推到了路边一幢农舍前的一小块空地上。四位司机都在向我走来。我立马掏出烟,并盘算着该向每人付多少报酬,可他们除三人边走边接了一支烟外,谁也没停下脚步。长沙口音边走边说:“你打电话叫修理厂来人吧!”当我走到自己车旁时,后面的车又鱼贯而来,我赶忙向每个驾驶楼挥手高喊谢谢,其中一辆农用车在我面前刹住,司机探出头来,我认出了是那位高坊口音,他用手作喇叭状向我喊道:“高坊镇上有汽修厂,你可以到那里喊人来修!”话音一落,车开走了。
我转身进屋,先进屋很久的妻子正在喝茶。我刚坐下,三十开外的女主人立即拿起姜钵擂起生姜来,不到一分钟,一杯热腾腾的姜盐芝麻豆子茶送到了我手上。女主人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笑出两个小酒窝。两口热茶下肚,我完全镇静下来,掏出手机向长沙众源汽修厂的王师傅拨通了求助电话,对方问清了我的方位,答应立即出发,估计个把钟头可到。
妻子见我衣服全湿了,向女主人借电吹风。女主人说她家电吹风坏了,旁边一位五十左右正在给怀中的毛毛喂罐子饭的大婶立刻接话:“我家有,你让妹子去拿,在电视柜左边抽屉里。”女主人正在看电视的十四五岁的女孩应声而起,向门外跑去。大婶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起身招呼我跟她走。我跟随她穿过公路向南走了几十米来到她家,这时那女孩已将电吹风拿出门了,大婶嘱她交给我后,有几分神秘地对我说:“我刚才忘了,我家房子才建好不久,政府还冒来安电表,她家里是安了表的。”我被安排在电视柜旁坐下,插好电吹风插头开始对着背上吹起来。大婶抱着毛毛进屋取出一件男式衬衣递过来,要我脱下湿衣换上干衣再吹。然后又唤出一位老奶奶将毛毛交到她手上,再又转身进了里屋,不一会便端出来一杯茶。她一手将我手中的电吹风接过去,一手将茶递给我。待我喝完那杯又热又香又辣的豆子芝麻姜盐茶后,衣服完全干了。热烘烘的衬衣刚接到手上,那股热气就传遍全身,连心也热了起来。我换过衣,打开手包抽出十块钱准备作为酬谢,大婶见状立刻阻止我,愠怒道:“你看我乡里人不来吗?”听了这话,我顿觉血往上涌,满脸热辣,只得尴尬地收回那张轻飘飘的票子,除了一连串小声的谢谢,我再也说不出什么来。大婶倒是话多:“出门在外,谁保冒个难处?我老倌和崽女也长期在外面打工咧。”我起身告辞,她又硬塞给我一把伞,“你不打伞又会淋湿,伞放在对门,住了雨我会去拿。”我如同挨了批评的学生,乖乖撑开伞,又说了一连串谢谢。
回到车旁屋内,一股辣香扑鼻而来。妻告诉我女主人煮了我们的饭,并悄悄告我:等会给她一百块钱。不一会,饭菜上桌了,主人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加上我们,五个人,六个菜:辣椒炒肉、韭菜花炒香干、蛋汤、空心菜、青椒炒干豆角、剁辣椒皮蛋。菜的味道很不错,饭也特别好吃。可女主人还说天黑落雨,丈夫又在长沙打工,不能上街买菜,小菜便饭对不住。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众源汽修厂王师傅带着三个徒弟赶到了,向房东借过雨伞斗笠草帽和手电就冒雨修起车来。若莫半小时,球头拉杆敲直了,轮胎复位了,车发动试开可以了,而他们四师徒都淋成落汤鸡了。幸亏妻子提醒我车上还有两瓶白酒,我赶紧拿来塞给了王师傅。他们让我走前,嘱咐我开慢点,有问题停在路旁等他们,他们到前面杨桥吃过饭就会尽快赶上来。
我和妻子又上路了,先是二十码,慢慢加到六十码,也不知怎么的,反觉得这明天要进厂修理的宝来比刚买来时还好开。我问起给钱给房主的事,妻说象打架一样跟女主人推让了好久,最后两张五十她硬只肯收了一张。
回到家,刚好八点。妻催我早点洗个热水澡上床休息,但我洗完澡后睡意全无,干脆叫过妻子和儿子泡起了工夫茶,谈起了下午的经历。全家人七嘴八舌议论开来:
四位司机主动帮忙换胎推车,为自已清除路障当然是主要动因,但嘱咐我别丢失物件、提醒我打电话到修理厂求助、告诉我高坊有汽修厂、个个淋湿一身却毫无怨言,这些与“清除路障”却丝毫不搭界呀!
众源汽修厂王师傅提供上路服务,目的当然离不开招徕客户,但在黑夜里冒雨驱车数十公里,饿着肚子淋着雨,就为获取一两百元的修理费,这值吗?
大婶说政府还末给自已家里装电表,要我到她家里吹干衣服,这确实有损公之嫌,但一位年过半百的农村妇女,她误以为电表是由政府装的,而政府对她来说,关系当然比邻居显得遥远而生疏,她当然把邻居的利益看得更重。至于她和对门房东女主人一样,对一个出门在外的陌生人那样慷概大方、照顾备至,能说她是损公肥私的人吗?
我后悔不该为了送同桌吃饭的老人而导致事故,但太太和孩子们都说,不愿成全别人的人,不见得会有别人成全你。这就叫吃亏是福,又叫好人有好报。
茶过七泡,味犹不减。一家子都庆幸我们倒霉之后遇好人,不幸之余得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