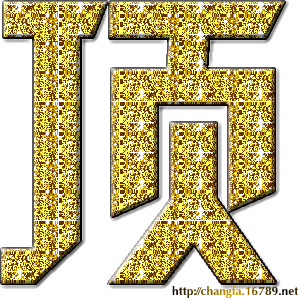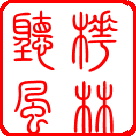那一年,我在文家市煤矿做临时工,挖煤掘进、打风钻都干过,三班倒单调而枯燥,一年到头几乎都被黑色包围着,刚二十出头的年纪,经受了再苦再累的体力劳动,心却还有向往浪漫的时候。
记得那年中秋节,我没回城里与亲人团圆,也没接受同事的邀请去赏月玩耍,喝酒看电影等,而是选择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手握洞箫吹起了酸不溜秋的曲子,箫独有的低沉绵长,显得是那么如怨如诉一般,尤其有月光的朗照,周围似乎披着一层柔软而缥缈的薄纱,使人宛若置身梦里。
这箫声本是让自己淡忘尘世烦恼,有带一点心有所思的牵挂。于是就不觉添了诗的意境:“一缕相思,醉了红酥手,青灯浅唱,燃尽指尖香”。没想到那一回的兴致,被我父亲单位的一位女同事的侄女儿见闻了。那位姑娘从侧面向人打听了我的情况后,就向她姨妈如此那般地坦言,那女同事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我父亲提出令他吃惊的事,父亲简直不敢相信那么漂亮又有工作的女孩会看上挖煤的儿子。可那热心的姨妈就不容分辩地张罗了一桌饭菜,在中秋后的礼拜天,把我和父亲请去赴宴。父亲在去之前把那女孩夸得跟天仙一样,可我却想别人再好也与我无关,我淡定的神态几乎激怒了父亲,我只好向父亲摊牌,我早已有了数来信往的女朋友,不过她也是知青,当时还在大山那边修地球而已(如今女友已成了我厮守半辈子的妻)。父亲当时很是惋惜的说:“你再怎么推辞,这餐饭还是要去吃,不然我都没法向人家交待。”
我硬着头皮与她们娘俩把盏对饮,那姑娘的确长相不俗,举止温柔,谈吐大方,她姨妈热情的布菜劝酒,饭后又拿出两张电影票出来,非要我们单独相处。那个年代相亲的如果能发展到看电影,十有八九能成功。可我如坐针毡地跟她看了一场电影后,依然惦记着回住处去跟女朋友写信,依然独自吹着洞箫,本就有些优柔寡断的我,唯独在对这个漂亮女孩缺少了热情,多了许多理智,辜负了人家的一片盛情。我为了避免与其见面尴尬,只好向煤矿辞了工,又回到了原来的生产队上,躲避着这一场艳遇,就如同躲避我不愿涉及的风花雪月。
我后来招工成家,奔波于工作和家庭之间,洞箫胡琴都被尘封多年。
十余年后,我忽然得到一个消息,南乡好友告诉我,当年那位一心想嫁给我的姑娘得绝症香消玉殒了。我悚然而惊,回想当年她的音容笑貌和充满迷惑的眼神,我脑海中久久一片空白。我破例取下沾满尘嚣的洞箫,为她于茫茫天际中,吹了一曲《红楼梦》中《冷月葬花魂》,一曲《你在天堂还好吗》,不过这不能证明什么,倒是添了一些伤感。
又多少个春秋如水流逝,琴依旧,箫还在,月光也还是那月缺有月圆,而人间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在继续一个接一个。我的双鬓也有了点点花白,也许生活的压力,总会使日子渐次瘦成一支箫笛,我与妻在平淡的光阴中慢慢变老,那份望月情怀已不再属于我这把年纪的人了,因此洞箫的一缕余音没有了“思念”二字的注释和浸润,当然也就少了许多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