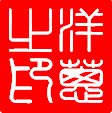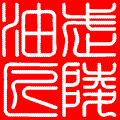1969年7月的一天,队上来了位20多岁的陌生青年人。
他1米78的个子,宽宽的肩膀,挺着直直的腰,炯炯有神的眼睛,长着一副络腮胡子,象貌倒还显得蛮英俊的。
“请问:雷伏蒂在吗?”那人一口纯正的长沙话。
“你是……?”我吃了一惊,我在厨房里弯着腰正准备做午饭吃;我新婚几个月的老婆雷伏蒂在大队部旁边的坝阳坪小学教书还没有回来。
“我是雷伏蒂最要好的朋友于小英的爱人萧楚凡,我是来靖县帮她迁户口回去的。”
虽然于小英我没有见过,但是她的基本情况从我老婆口中不止听过一百遍:她俩从小就住在长沙市经武路松桂园附近,既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又是天天形影不离;1965年10月8日,她俩没有跟随学校的同学们下放到怀化县,而是跟随三公里办事处的青年们一起下放到靖县铺口公社坝阳坪大队崇孔生产队当知青。
哦,这下子我才知道:今日来的长沙陌生青年叫萧楚凡,是我爱人玩得最要好的朋友于小英的丈夫!
平时好客的我当然把他迎进了屋里,并热情的招待他。
下午放学了,雷伏蒂回来了,她同样既高兴又热情的向萧楚凡问长问短,想知道好朋友于小英更多的情况。
当时队上知青转的转了点,有的呆在长沙还没有回来,只有我们夫妻俩在队上“抓革命,促生产”。
当时正是7月份,田里的稻谷已经打苞了,正是靖县农村守野猪的时节。
晚饭后,当他得知我要去守野猪。他好奇地说:“我也要和你去守一晚野猪看看,让我体验体验你们知青的生活!”
我没有拒绝他,我打着火把引萧楚凡跟随着我一起来到了一个叫岩门口的地方,那里几十亩田里的稻谷是这个时期野猪经常光顾的。
我在岩门口对面的乱葬岗子上面搭了一个守野猪的棚子。黑暗中时常有“鬼火”在我身边飘来飘去,我却一点都不害怕!
我生起了一堆熊熊的大火和萧楚凡坐在棚子外面边抽烟边聊起了天。
我进一步的知道:他是复员军人,现在在浏阳磷矿汽车队开车!
那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
于小英的爸爸早已过世,于小英的妈妈一个人被迫下放到汨罗县新市机械厂。返城后的于小英也随着妈妈的下放住到了汨罗县新市,母女俩在一起相依为命。
萧楚凡是于小英远房的表哥。1963年在昆明部队当兵的萧楚凡受桃江亲戚的委托,到长沙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于小英的爸爸和妈妈;那时候于小英才14岁,萧楚凡对这位远房的表妹非常有好感,并向于小英的爸爸和妈妈表示过今后要娶于小英做堂客!而于小英那时年纪还小,每当萧楚凡从部队探家路过长沙来看他们全家时,于小英看见萧楚凡进来了就羞答答的躲了起来。
于小英下农村时,还在部队当兵的萧楚凡已经24岁啦。
16岁下农村的于小英这时候已经是位楚楚动人的大姑娘啦。
但是这几年文化大革命这一搞,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一切都乱了套啦!
于小英回到了被迫下放到了汨罗县新市机械厂的妈妈身边。 1968年冬天,户口还在靖县的于小英终于和萧楚凡结婚了。
就这样,萧楚凡和我在守野猪的棚子里度过了那令人牵挂了37年的难以忘怀的一晚。
第二天上午,萧楚凡在队上结清楚了于小英的往来账,向我和雷伏蒂告辞,他谢谢我们的热情款待;拿着生产队和大队开出的证明就到公社去办理有关迁移手续去啦。
他就这么一走,就是几十年……
1978年,我们回城了。
联系上了的朋友一拨又一拨,而于小英,萧楚凡夫妇始终音讯全无。
随着经武路的拓宽,雷伏蒂年年要和我说起要找于小英和萧楚凡。
而我也就只晓得:萧楚凡1969年是浏阳磷矿汽车队的司机。
是湖南知青网,是浏阳的知青朋友们帮我们园了这37年苦苦冥思的梦!
今天,梦已经成为了现实!
找的不是亲生父母,不是兄弟姐妹,而是我们的知青朋友!这才叫真正的知青情结啊!
东方兄和80个知青娃等浏阳知青朋友帮我和雷姐找到了他们二位。
我用此文来表达我对大力支持的各位朋友的感激之情。
另外我还知道萧楚凡大哥和我好多的知青朋友都有着深厚的知青情结。
里面包括了我许多打篮球的熟人朋友,如:米司令(安乡知青),小弟,黄仁,张胖子(靖县知青),西瓜皮(长沙东方红农场知青),小毛,丁老板(岳麓苗圃知青),萧楚凡还是丁老板丁平志的学开汽车的师傅呢……
当然,还有那浏阳的我不认识的知青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