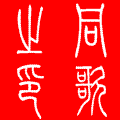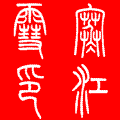个人不由得十分紧张,我想扔掉包就跑,被罗江喝住了。但仅走一段,那农民拐弯了。——原来是我们多心。
那天我们满载而归,三个书包装了八只鸡。晚餐杀了二只,直把我们撑得十二点才入睡。谁知第二天清晨,张海带着团支部书记把剩下的鸡全部搜走了,我们三人还在知青大会上作了深刻检讨。
“真对不起三位兄弟。”我回忆起张海当时的窘迫镜头:他哭丧着脸,近视镜取下又戴上,戴上又取下:“心里不安,横竖睡不觉。这样吧!你们扣罚的工分,我赔。”
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宽容了他。他是那种骨子里生来正统的人。我们坐船不买票,上馆子不掏钱,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的这些恶习。张海从来不沾边。但小弟讨人喜欢,是我们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种的菜长势良好,做饭手脚麻利,早上出工前,他魔术般地变出四碗面条;又唱着歌,一眨眼便把房间、床铺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有他爱好音乐,经我们传唱,知青中广为流传的《南洋民歌》、〈〈夜半歌声〉〉及〈〈故乡寒夜曲>>等这些歌曲也不知张海从那里学来的?
桌上端来一壶茶、二碟瓜子。老板娘勾着腰问我们是否上菜?这才把我们从遥远的思绪拉了回来。二十年了,因交通闭锁,这儿一切依旧。如果说变化:当年风韵撩人的女掌柜如今已是徐娘半老;门前的歪脖子榆树已长得高大挺拔、冠盖如云;拐角照相馆前那条拖拉机一开过,便漫天灰尘的土路现已铺上了柏油------
傍边饭桌陆陆续续座满了人,张海夫妇仍未到来,老板娘说:“鲤鱼渡的班船刚过,人没来,那只有等明天啰!”说着她又用手指了指江面上那座焊花四溅、紧张施工的大桥,补充道:“年底就好了,鲤鱼渡通车,听说这座桥是一位国外创业的知青老板捐的款。”
罗江给我们各递一支烟,如今他和往昔判若二人:岁月已洗去了当年的恶习,他出言卑谦、待人随和。目前他在省城火车站摩托车送客,生活平顺。但脑中固有的观念,他仍是我们的头,他坚持按当年约定,12时正点开餐。
这当口,刘湖打开了话匣子,讲起了我们差点忘了的一件趣事:
冬修水利,我们大队负责雁鹅湾一段堤坝加高。工地上:千军万马、热火朝天。挑堤的队伍有如一串串蚁阵望不到头。息工时,我们四人到一处池塘洗手,突然,张海一声惊叫,让我们骇了一跳。原来是他无意中翻开一块石板,窜出一只脚鱼,只见它浑身黝黑,以极快的速度冲向池塘。情势突然,我根本来不及作出反映。恰在此时,罗江像一只山猫,一个漂亮的猛扑,半途中,便把脚鱼截住了。好家伙!这是我平生所见的最大的脚鱼,足有五斤重。
挑堤结束,我们回家,张海把脚鱼洗净切块,配以佐料,放入火锅,同时将草靶塞入灶膛,将柴草烧旺。借着熊熊火光,他着迷地看着一本无线电杂志------
不久,刘湖收工,老远就闻到一股烧焦了的糊味,打开锅盖,整个脚鱼都烧成了黑炭。
“天啦!惨不忍睹。”刘湖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情景:“脚鱼倒在水凼里,狗都不吃。” 确实,这件事我们笑谑了张海半个月,把“白面书生”喊作“黑炭先生”。
——人生短暂、岁月悠长。可以说,我们曾把一段青春淹没在这里,所有对与错、苦与乐的往事都成了记忆中的美好回忆,友谊也成了精神上的宝贵财富。这里同样是没有围墙的大学校,我们可以面对面地阅读生活这部百科全书;从这里走出去,任何苦难我们都可以从容面对,命运中一缕阳光我们却百倍珍惜。
十二点开餐只差五分钟了,热气腾腾的菜肴也是按当时的品种端上了桌,此时:三位女士急不可耐地埋怨开来:“还要等什么?这书呆子把此事早给忘了!”“可能混得差,不好意思来------”但我们兄弟三人仿如心灵感应,默不吱声。
突然,一辆吉普车“嗞”地停在饭店门口,走下一位公务员模样的中年男子。他打开皮夹,抽出一封信:“请问,那位是罗江?”
“什么事?”
“这是你的信,我是县外事办的,县长要我准时送到。”
打开信笺,字数不多,我们沉思良久:
“江、河、湖兄:如面。要务缠身,未能践行,望请恕罪。早年投邮数封,因旧城改造,终难联系。忆当年,兄弟们禾圹摔跤、河堤论字;秧丘犁田、月夜捕蛙。总是魂牵梦绕,恍如昨日。目前我在美国加洲硅谷办了家电子公司,因年底鲤鱼渡大桥剪彩,我将回国。屉时知青小屋重聚,兑现我分手时承诺。海弟。”
那天我们满载而归,三个书包装了八只鸡。晚餐杀了二只,直把我们撑得十二点才入睡。谁知第二天清晨,张海带着团支部书记把剩下的鸡全部搜走了,我们三人还在知青大会上作了深刻检讨。
“真对不起三位兄弟。”我回忆起张海当时的窘迫镜头:他哭丧着脸,近视镜取下又戴上,戴上又取下:“心里不安,横竖睡不觉。这样吧!你们扣罚的工分,我赔。”
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宽容了他。他是那种骨子里生来正统的人。我们坐船不买票,上馆子不掏钱,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的这些恶习。张海从来不沾边。但小弟讨人喜欢,是我们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种的菜长势良好,做饭手脚麻利,早上出工前,他魔术般地变出四碗面条;又唱着歌,一眨眼便把房间、床铺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有他爱好音乐,经我们传唱,知青中广为流传的《南洋民歌》、〈〈夜半歌声〉〉及〈〈故乡寒夜曲>>等这些歌曲也不知张海从那里学来的?
桌上端来一壶茶、二碟瓜子。老板娘勾着腰问我们是否上菜?这才把我们从遥远的思绪拉了回来。二十年了,因交通闭锁,这儿一切依旧。如果说变化:当年风韵撩人的女掌柜如今已是徐娘半老;门前的歪脖子榆树已长得高大挺拔、冠盖如云;拐角照相馆前那条拖拉机一开过,便漫天灰尘的土路现已铺上了柏油------
傍边饭桌陆陆续续座满了人,张海夫妇仍未到来,老板娘说:“鲤鱼渡的班船刚过,人没来,那只有等明天啰!”说着她又用手指了指江面上那座焊花四溅、紧张施工的大桥,补充道:“年底就好了,鲤鱼渡通车,听说这座桥是一位国外创业的知青老板捐的款。”
罗江给我们各递一支烟,如今他和往昔判若二人:岁月已洗去了当年的恶习,他出言卑谦、待人随和。目前他在省城火车站摩托车送客,生活平顺。但脑中固有的观念,他仍是我们的头,他坚持按当年约定,12时正点开餐。
这当口,刘湖打开了话匣子,讲起了我们差点忘了的一件趣事:
冬修水利,我们大队负责雁鹅湾一段堤坝加高。工地上:千军万马、热火朝天。挑堤的队伍有如一串串蚁阵望不到头。息工时,我们四人到一处池塘洗手,突然,张海一声惊叫,让我们骇了一跳。原来是他无意中翻开一块石板,窜出一只脚鱼,只见它浑身黝黑,以极快的速度冲向池塘。情势突然,我根本来不及作出反映。恰在此时,罗江像一只山猫,一个漂亮的猛扑,半途中,便把脚鱼截住了。好家伙!这是我平生所见的最大的脚鱼,足有五斤重。
挑堤结束,我们回家,张海把脚鱼洗净切块,配以佐料,放入火锅,同时将草靶塞入灶膛,将柴草烧旺。借着熊熊火光,他着迷地看着一本无线电杂志------
不久,刘湖收工,老远就闻到一股烧焦了的糊味,打开锅盖,整个脚鱼都烧成了黑炭。
“天啦!惨不忍睹。”刘湖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情景:“脚鱼倒在水凼里,狗都不吃。” 确实,这件事我们笑谑了张海半个月,把“白面书生”喊作“黑炭先生”。
——人生短暂、岁月悠长。可以说,我们曾把一段青春淹没在这里,所有对与错、苦与乐的往事都成了记忆中的美好回忆,友谊也成了精神上的宝贵财富。这里同样是没有围墙的大学校,我们可以面对面地阅读生活这部百科全书;从这里走出去,任何苦难我们都可以从容面对,命运中一缕阳光我们却百倍珍惜。
十二点开餐只差五分钟了,热气腾腾的菜肴也是按当时的品种端上了桌,此时:三位女士急不可耐地埋怨开来:“还要等什么?这书呆子把此事早给忘了!”“可能混得差,不好意思来------”但我们兄弟三人仿如心灵感应,默不吱声。
突然,一辆吉普车“嗞”地停在饭店门口,走下一位公务员模样的中年男子。他打开皮夹,抽出一封信:“请问,那位是罗江?”
“什么事?”
“这是你的信,我是县外事办的,县长要我准时送到。”
打开信笺,字数不多,我们沉思良久:
“江、河、湖兄:如面。要务缠身,未能践行,望请恕罪。早年投邮数封,因旧城改造,终难联系。忆当年,兄弟们禾圹摔跤、河堤论字;秧丘犁田、月夜捕蛙。总是魂牵梦绕,恍如昨日。目前我在美国加洲硅谷办了家电子公司,因年底鲤鱼渡大桥剪彩,我将回国。屉时知青小屋重聚,兑现我分手时承诺。海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