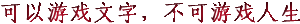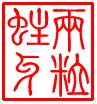74、75年已接近上山下乡的后期,从长沙下放的老三届知青已走得差不多了,但也还有一小部份未能离开农村,他们大多都散落在各个村落里,当时叫生产大队,年龄也都有二十四、五了。
当时我所在的胜峰公社就还有十来个,其中也不乏有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的,主要还是嫁的一些回乡知青或退伍回乡军人,我还见到过其中的一位。
那时我在一所村办小学当民办老师,学校放暑假,老师回生产队参加“双抢”,我记得是叫龙秀大队,具体是哪个生产队记不得了,早就听说一个长沙女知青嫁给了队上的回乡知青。一天,我们几个本县下乡的知青和几个老农正在田间劳作,中途休息时,那位回乡知青的父亲,邀请我们到他家去歇气,并说他们家也有知识青年,言语中透出一种自豪感(这是其他几位老农背着那位回乡知青的父亲,把这种感觉告诉了我)。
他家刚好离我们劳动的地方不远,于是我们几个就到了他家,他非常客气地给我们端来一罐凉茶,并装给我们一人一支当时一般农民很少抽的纸烟。这一看就是当时农村比较殷实的家庭,房子虽然是土砖,但盖的是瓦,房子高高的,也很宽敞,并收拾得很整洁,房子四周都栽着高大的树木,屋后还有一个小柴山,虽然是盛夏,屋内却很阴凉。
我们没有见到他儿子,据说是抽到公社征粮去了。不一会儿,从西边后厢房里走出来一个女青年,个子中等偏高,长得比较丰满(但决不是胖),一看就不是当地农村妇女,穿着白的确良衬衣,隐约可现里面穿着当时农村一般没有的胸罩(请原谅,决非非礼,而确实是夏天衣着比较单薄),脚上拖着一双泡沫塑料拖鞋。
我们是坐在堂屋里,她径直走过我们面前,进到对面前东厢房里去了,也没和我们打招呼,直到我们离开她家也一直未出来。这在当时,双抢时节,人们都在上蒸下煮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熬日子,相比之下,这位女知青也算是得到了一种庇护吧。
现在有一句时髦的话,叫“活在当下”,是否那位女知青,或者那类女知青当时就理解了这句我们现才知道的话的内涵呢,不得而知。(因为真正因响应当时的号召嫁给农民,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彻底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做填平三大差别的小石子的人必竟还是极少数。我还亲历过一次知青点的带队干部坚决阻止下乡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事例,这也说明除了懵懂无知或受迫害被利用以外,主要还是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当时我所在的胜峰公社就还有十来个,其中也不乏有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的,主要还是嫁的一些回乡知青或退伍回乡军人,我还见到过其中的一位。
那时我在一所村办小学当民办老师,学校放暑假,老师回生产队参加“双抢”,我记得是叫龙秀大队,具体是哪个生产队记不得了,早就听说一个长沙女知青嫁给了队上的回乡知青。一天,我们几个本县下乡的知青和几个老农正在田间劳作,中途休息时,那位回乡知青的父亲,邀请我们到他家去歇气,并说他们家也有知识青年,言语中透出一种自豪感(这是其他几位老农背着那位回乡知青的父亲,把这种感觉告诉了我)。
他家刚好离我们劳动的地方不远,于是我们几个就到了他家,他非常客气地给我们端来一罐凉茶,并装给我们一人一支当时一般农民很少抽的纸烟。这一看就是当时农村比较殷实的家庭,房子虽然是土砖,但盖的是瓦,房子高高的,也很宽敞,并收拾得很整洁,房子四周都栽着高大的树木,屋后还有一个小柴山,虽然是盛夏,屋内却很阴凉。
我们没有见到他儿子,据说是抽到公社征粮去了。不一会儿,从西边后厢房里走出来一个女青年,个子中等偏高,长得比较丰满(但决不是胖),一看就不是当地农村妇女,穿着白的确良衬衣,隐约可现里面穿着当时农村一般没有的胸罩(请原谅,决非非礼,而确实是夏天衣着比较单薄),脚上拖着一双泡沫塑料拖鞋。
我们是坐在堂屋里,她径直走过我们面前,进到对面前东厢房里去了,也没和我们打招呼,直到我们离开她家也一直未出来。这在当时,双抢时节,人们都在上蒸下煮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熬日子,相比之下,这位女知青也算是得到了一种庇护吧。
现在有一句时髦的话,叫“活在当下”,是否那位女知青,或者那类女知青当时就理解了这句我们现才知道的话的内涵呢,不得而知。(因为真正因响应当时的号召嫁给农民,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彻底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做填平三大差别的小石子的人必竟还是极少数。我还亲历过一次知青点的带队干部坚决阻止下乡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事例,这也说明除了懵懂无知或受迫害被利用以外,主要还是取决于个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