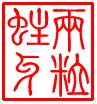风雨洞庭 一,启航 69年元月,小寒后几天,天添了寒意。家属宿舍周围一股郁闷、焦虑的气氛。我的同班好友大都在一星期前去了华容插队落户,心里空荡荡的。我去派出所办加粮手续,遇到同学第二批去华容,扛箱背被,送送他们,也解解闷。 轮船要从河东的轮渡码头出发。船上有几个学校的学生,挤得像难民一样。我有个小学一年级的女同学,她父亲跟我父亲谈得来,我到她家走的也多。她胆子小,爱哭。有一次烤火,把竹制的烤火罩烤烧了,吓得只喊哥哥。我家搬到河西后,好几年没有联系,想起来与两家都有些历史上的政治麻烦,不便交往,听说后来她考到4中,还是14中读书了。那天见到她,是在船尾部的洗漱间。我匆匆推门,没拴,见到一女孩伫立在百叶窗口旁,背对着门抽泣。待她回头,我惊讶地喊了一声她的乳名——她已经出落成一个高挑的女孩。她看了看我,没有应声。我问她是送同学还是自己下乡、下到哪里,又问她的行李在哪里,还问她的爸爸妈妈好不好,家里人怎么没来送她,并且说我是来送同学的,要不要我帮忙。她绷着脸,红着眼,不理我,冲走了。我有些恼火。等缓过神过来,再去找她的时候,不见她了。我想她是送同学的,冲回家去了。 船舱里乱糟糟,到处找行李的,帐竹篙绊脚摔跤的,木头衣箱突然踩垮了的,还有竹杆卷起红旗,刚刚宣过誓的,以及我这种混进船舱送同学的,不像一次很骄傲的起航。 “轰隆轰隆”轮船生火了,汽笛“呜呜”几声催促,船上的学生们好像突然明白,离别亲人的时刻实实在在来临,还没有来得及向码头上的送行的亲友道尊重。豪言壮语猝然停落,短暂的沉寂里过后,有几声偷偷的抽泣,突然传来女生“哇”的一声嚎啕大哭,好些女生哭作一团,整条船摇晃着,向码头一方倾斜。男生还有些女生或不屑的、或迷惑的,或噙着眼泪转过头去的,一个个默默不作声。有的女生拥挤到船窗栏杆边,凄凉呜咽着:“妈妈啊”,“我的妈妈啊”。码头上,送行的锣鼓丁子“咚咚锵,咚咚锵”幸灾乐祸瞎参合,几只破铜管喷出阴阳怪气的欢送曲。 码头工人拉长嘶哑的声音喊:“要开船哒,送客的快下船啊。”我混在船舱里,心里越发不踏实,心想,下乡是免不了的,还不如现在就到华容去,那里有我的同班同学。我悄悄呆到不显眼的人群里,摸了摸裤兜,里面只有我办加粮手续的户口本和粮折。 精干的大男生开始高亢领唱,几个学生跟着唱起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呜——”,汽笛一声长啸。船憋足了劲“扑嗤扑哧”几声,搅起船尾 “哗哗"黄浪,拉着我们缓缓去向那个影响我们未来一生的湖乡广阔天地。熟悉的古城小巷,渐行渐远,消失在冬的迷茫中。 二,夜泊麻花尾 轮船慢腾腾过湘江、入洞庭湖,到了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平原小码头,天已经快黑了。我们迷迷糊糊上了堤,迷迷糊糊被拖拉机和解放牌卡车送到几十百巴里远的小河边。河里停着十几条木船,河边星星点点的手电筒亮光萤火虫似的闪来闪去,站着十多个农民,他们是来接知青的。 “你是知识青年吗?”一个扎起深黑色头巾的中年农民轻轻的问我,我第一次被农民称呼知识青年,从此接受了这个称呼。我和两个同校的女学生被安排上了他的木船,知道他姓魏,是生产队长。 湖乡的夜墨黑墨黑,空空荡荡,静得心悸,只有木桨划水“哗、哗”轻轻荡涤声,船身擦过湖草发出的“喳喳”声。木船走过了好多湖汊沟渠,几十里水路,停泊在生产队所在的叫麻花尾的湖边小村。 村民们提起马灯、打起手电筒,迎宾似把知青接到各自家里安顿。我的主家(房东家),烧好了热水,煮好了甜酒粑粑,一口一个:“长沙街上来的伢妹子,到我个乡里来受苦,前世作哒孽。”主家的小孩梦里醒起,不时探探头好奇打量。我吃得饱饱的,睡在雕有八仙飘海的旧式木床上,干干净净,暖暖和和,沉入了梦乡。 我的他乡梦开始了。还梦见了爸爸妈妈,妹妹弟弟。我不是离开他们才两天吗? 三、微澜初起 麻花尾是洞庭湖平原北部一个向华容西湖突起的尾状盲端,住着几十户人家。这里的农民称自己为南边人,大多是洞庭湖南边益阳、沅江的移民后裔,保留南边人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他们守望大片肥沃的湖田、丰富的芦苇篙草以及满湖的鱼虾,野鸡野鸭,过着相对封闭安逸的农耕渔狩生活。 已近农闲,冬修湖堤的青壮农民还没有回,留在队里的农户走人家、烤火,谈天说地,打糍粑,做甜酒。大雪纷飞的时候,一个同班好友,也“投奔”我这里来。还打听到到我的同班好友好多下放在插旗公社官山大队,有大十几里的路,同大队的知青大多也是本校同学。知青间着实热热闹闹串了一阵门。 一个多月后,回长沙过年。我挑起一个大糍粑,差不多一斗糯米打成,还有糯米、芝麻、黄豆、麻油一大担,引起家里、邻居一阵惊喜,说是我下了一个好地方。这些年货是队里预支给我们的。父母庆幸我做了一次明智的选择。他们对我生活中的重大决策从不抱怨。 隐隐约约听到有下乡青年在农村的不愉快的遭遇,还听说有家长靠关系,躲避子女下乡的传言,我将信将疑。不久,我的妹妹,一个懦弱的女孩,插队到了湘西靖县山区,想家几乎想得发疯,72年转到了华容我下放的那里,后来读了卫校,就业成家,信了基督。我的弟弟下放到长沙县,70年代中期,被招工到长沙纺织厂当了厨师,如今,他两口子承包长纺食堂,经营的“长纺馒头”在河西一带有些影响。 过年后,我背起衣被,回到麻花尾。冬修水利的劳力走了,过年的气氛仍然较浓,主家大婶说年要过到插田。听说小年边上,有个长沙女知青来问过我,还给我留了条子,我没有看到条子。过年时父亲说过,那个小时同学女生的家早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主家的主妇,一个善良的中年妇女,一边拉风箱,一边嘟噜:我屋里崽,要讨堂客,她开口就要上海牌缝纫机,我乡里人哪里买得到啰。我感觉,人们的生活逐渐回到了过年前的实际水平,红锅子炒菜,也有的。我隐隐约约感觉,气氛有些异样。队里一个基干民兵,瞪着眼睛要我老实些,口气有点像对五类分子。我想申辩,还把补办的下乡手续交给魏队长。他说:“别队的知青传起,你家里阶级高了一些,到乡里来投机镀金的,”叹了叹气:“莫信他那多,你自己好点做事情就是。”又补充:“你来的时候,冒办手续,我看了你的户口,粮折子,是我答了白的,分得别人冒得么子空话讲。” 四,茅屋为秋风所破 过了半年,我们从主家搬到队屋(队部)里住,主家千叮咛,万嘱咐,不时来看看我们。一碗辣椒萝卜一碗酸菜往我们这儿送。两个女知青后来被招工了。我的同班好友和我一样,规规矩矩,爱点“之呼者也”。他做事认真,有条不紊; 我有些毛糙,想法比他多点。我们跟村里人大都相处很好。他们调侃称我“王夫子”,称他“章夫子”,又感觉有些不恭,朝我们不休修边幅长长的毛茸茸的青春胡须看,改叫“王胡子” “章胡子” 春耕的时候,湖田淤泥太深,只能人背犁。插田最怕提不起脚,越陷越深。几寸长的蚂蟥,紧紧箍在腿上,血红血红,也懒得去管。 夏天双抢时节。极为开阔的湖田长不了树,离房屋都很远,找不到遮阳挡雨的地方。累及了,头盖斗笠,睡到田埂上蚕豆杆、和深深的杂树野草下,也能嚷着,梦回故乡。 瘦小的蔡家满爹,单身一个,不善言谈,常带我撑船、划桨、打湖草。一天累了,船靠在篙草芦苇边,耐不住我纠缠,蔡家满爹低声唱起:“人在世上冒得搞啊,比不得墙头一颗草。草死逢春又发生啰,人死一去影无踪。”老泪一抹:“你个王胡子,莫信我唱的,街上人有出头,莫耽误自己啊。”我不敢追问满爹的身世,这后半句叮嘱是记住了。
秋天的雨夜,平原的湖风大得吓人,像火车隆隆呼啸,我俩卷缩在一个只有两间房的茅屋里。那是队部的凉亭,平时用来看护仓库的人住,或遮阳挡雨。用小树木头楠竹做桩檩,茅草铺顶,牛屎稻草湖泥敷在芦苇杆扎起的壁上竖起来的。风夹着雨,大摇大摆从屋顶墙壁缝隙串进小屋,打在脸上,茅屋随风摇摆。我有点畏,一摸被子湿了,神经质地坐起,叫了一声:“啊,屋子要倒了吧”。章夫子摸到火柴,瑟瑟地将煤油灯一次次点燃,一次次熄灭。我们从灶台上找到一盏马灯,两人忙着,灯火点燃了。灯光微微的,挺立着,增添了一份安宁、藉慰。
五,洞庭湖的麻雀
魏队长把我俩安排回到生产队队屋的厢房。队屋是用湖泥砖砌的,有厚厚稻草顶的,大小七八间房的大茅屋,也是队里办公室,兼会议大厅和粮食、农具仓库,还有牛栏猪栏等。队干部说,长沙知青来的时候,几个队过抢。他们料定长沙知青呆不了多久,队上吃穿住不成大问题,知青的安置费和竹木指标,是他们修砌队屋最紧缺的,可惜他们一时把我们留在了在秋风中摇曳的小茅屋。
湖区的防汛抗旱,冬修河堤,是对“街上人”,体力和毅力的考验和磨练,有蛇蜕的垂死和重生感。我创造了一趟挑200斤水泥艰难上堤防汛的个人最高纪录;农民一般一天吃两餐饭,我还创造了连续三天一餐吃一斤米的饭的个人最高纪录,至今还留下吃饭特快的饿相。花南窖湖堤发现险情,劳力——我们也是生产队派出到防汛指挥部干活的劳力——都是抢险战士。干部自己挑着大担,一边叫着,催着,骂着。我上坡稍慢,屁股被踢了一脚,不是干部,是同队的好伙伴干的。堤内垸里有着农民几乎所有的幸福、梦想和希望。大堤一破,就是势不可挡的家破亡。
蛇蜕过后,我几乎被同化为地道的南边人,跟他们一起撑船、背纤,到粮站送公粮。有次还送粮到县城里,累极了,和老乡一起,挟着扁担,大斗笠遮脸,流浪汉一样,和衣熟睡在街边屋荫下。街上人像嫌弃叫花子似的喝斥送粮人。这是我不愿提及的往事,我还是写了,留给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
远近的长沙知青一批一批走了不少,有时来一个招工的或家长,带几个招工指标,就领走几个知青捎上几个当地农村青年(我并不反感后者现在也理解前者)。我几次被生产队推荐招工,最后一次,做完了所有的告别仪式,第二天准备走,被告知招工指标被顶替,又告吹了。
章胡子轻轻陪伴在我的身旁,默默安慰、倾听我的委曲。我又知道这次他把自己的招工名额让给了我,两头失塌,也没有走成,愤怒地向上级写信鸣不平。天还没有亮,我走了十几里烂泥路赶到公社所在地大乘寺。
没有看到普度众生的大乘古寺,只看到高高的屋台上围起一幢“口”字形公社办公大院。知青办的一个当头的,胡乱看了一下信,一搓,扔到地上。看我要发作,轻蔑一哼:“要翻天吗?”又拍桌子:“老子,洞庭湖的麻雀,见过风浪的。”章胡子怕我闯祸,随后赶来。一把拉住我,说:“算了,算了,搞他们不赢”。我只得一顿骂骂咧咧 ,愤愤而归。
半年多后,这只戴着退色军帽的“麻雀”不知犯了什么忌讳,撞了哪路神仙,被单位下放,掉到了洞庭湖里,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不久,修大乘寺港堤的时候,章胡子被招到一家军工厂当了工人。他兢兢业业、克己待人,至今仍然是我亲兄弟一样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