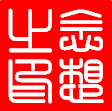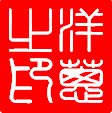送粮谷
那一年,我20岁。在生产队当保管员。
晚稻收割后,开始送粮谷(交公粮)了。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送到粮站的粮谷老是被扣称。不是说瘪壳多,就是说水分高。我把谷子晒了又晒,厢了又厢,送粮谷的回来还是说被扣称。我恼火的很,决定自己去看看。
早起我出了担谷子,准备上街。临走前看看自己的打扮:脚登轮胎底草鞋,穿一条从满伢子那借来的黑棒布裤子,一件烂棉衣拦腰系根草绳,头发快盖过耳朵了。还行,我就是要打扮成农民样范,到粮站港(讲)起蛮话来没忌讳。
百多斤的担子从队上我一气挑上雷打坡,脚杆子劲十足。这里插一个小故事:90年代初,我带一帮人上泰山,快到南天门时遇到几个天下闻名的“泰山挑夫”。我一时兴起和大家赌狠,说我能把那人的担子挑上山,谁都不信,说你戴个眼镜,白面书生,哪里挑得动。我和那个老乡商量,起先他不肯,怕我摔了他的砖,(四十多口青砖)怕我耽误他的时间。我说押一百块钱在你手里,摔了我赔,他才同意。我杀了杀腰带,挑起砖,连超几个挑夫,一气挑上了山。着实出了回风头。赢了同事两包“大中华”。这是后话。不过当年我年轻,走山路,挑重担是家常便饭,就是有脚杆劲。
十五里山路我只在雷打坡凉亭里歇了一气,就到了梓桐宫(梓桐宫还在吗?)粮站。过地磅时里面的小姑娘报称:“刨皮128斤,扣3斤水,125斤。”我火气一下就上来了:“郭燥的谷,你眼睛打蚊子可达,楸都没楸就扣水!”“你们彭家团谷子不燥,都要扣”小姑娘眼皮都没抬,还在打毛线。“你娘卖白,我俩个把谷滩得坪里晒,到下半日失一斤我恰噶生的!要是冒折称你就是刘文彩的女!”我讲起蛮话来达。“找起你们领导来,我到要搞个清白!”“算答算答,我同你港不清。”小姑娘服软了,看来还是要行蛮。看着小姑娘写票我还不依不饶:“跟老子好生写起,莫欺负我们贫下中农没认得字!”
谷子进了仓,我挑着空萝往外走,正为自己的表演暗自得意,忽听屋里的小姑娘小声对别人说:“那个剁脑壳的是个长沙知识青年…”完了,我还是败露了。
从此,我们队上的粮谷再也没扣过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