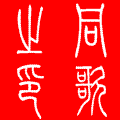沙阳小学原在6队张家台上的几间破烂不堪的茅舍里,简陋得不能再简陋。在这里,三五个老师和百来号学生终年在没有基本教学设施的条件下渡日,成为安康公社几乎被人遗忘的学校。由于条件实在太差,因此,公社先后派来过的几个公办教师都呆不了多久便都离去。
1971年,大队痛下决心,改变这种面貌。于是,沙阳大队自己掏钱,本土岩匠汪国勋自己设计、各队抽调社员自己动手盖起了一排新房,作为卫生所、学校和代销店。这是沙阳历史上第一幢红砖瓦屋。在沙阳这块贫瘠的、安康最偏远的地方盖上这么漂亮的房子,甚至超过了临近的赫赫有名的黄茅洲学校(杜家大队学校),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也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的体现,是对于农村教育事业的重视吧。
1972年春季招生开始前,根据需要学校要增加一名民办老师。在党支部研究人选当中,免不了各种利益的平衡难以达到。最后,基本上确定抽调我这个不牵涉各方利益的知青到大队小学去当这个民办老师。事后,大队支部的某委员也向我通报了这个消息,要我作好准备,春节之后开学就去学校。去学校教书,这可是我十分向往的美差!生产队这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我已经扎扎实实干了三年,差不多无法忍受了,加上我也算是教师世家出身吧,子承父业,何乐而不为!如果父母亲得知,肯定也会很高兴的。
果然不出所料,父母亲接到我的来信之后,心情非常激动,当即写信表示祝贺,并表示要把我父亲自己手上的一块上海表送给我,好让我上课掌握时间;同时向我交代了诸如当教师要如何为人师表,要如何加强自身的学习之类的嘱咐。不久,知青周某从长沙回乡,父亲就将他的这块旧手表给我搭过来了;父亲告诉我,这块表是一年前他用20张“公分劵”和125元排队买来的,要我好好爱惜,
在那个年代,有一块手表产生的轰动效应不亚于今天谁买了一辆“宝时捷”名车。我的心里美滋滋地,这是我20多年来最值钱的东西,且戴上它的意义还远不止如此!于是,也常戴着它去挑草和田里开沟。就这样,学校还没去,我就戴着手表“招摇”的消息不胫而走;泥腿杆子可能投来羡慕的眼光;但是,还没有成为“有表阶级”的某些干部们可能心里不舒服;当初挑选民办老师时的利益丧失者也正好抓到了把柄。不久,有小道传来我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传言,时任大队团支部书记的寒江雪悄悄地告诉我,要我注意。
开学以后,我当民办教师的资格果然被莫名其妙地取消。抽调的人换成了大队副书记杨某某的儿子杨S保。就这样,69年株冶招工未去成,这次当民办老师又与我无缘了。
“组织上”的决定时常成为戏弄人的事在那年头也算家常便饭吧!作为“袜底子不干净”的我当然不能有任何怨言。认命,我们不是吃“楼活饭”的料子!
杨S保走马上任第一个学期,无奈高小毕业不几年的这个副书记的儿子实在是太不为貧下中农争气。72年一年还没有搞上头,这个“杨老师”强奸和猥亵10几个小学生的丑事就东窗事发,搞得全公社教育系统沸沸扬扬。后来,公社和大队成立了“专案组”进行了一段时间调查落实,杨某的案子最后得到了确认。
秋收以后的一天,公社武装部长袴着一把驳壳枪,带着一根麻绳来到沙阳学校,由大队治安主任带领,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杨五花大绑押走了。
杨被判刑三年,学校又缺老师,公社教革组几年没有派公办老师来过,现在也没有人派。于是,大队有干部又提出当初本来就是想抽调知青Q某的,这次还是要他来。
大队通知我割完晚谷以后就去学校,当年我正担任生产队会计,没有俟到做年终决算,就匆匆上任了。
虽然从年头到年尾拖了我大半年的时间,我本来已不抱希望,但这迟来的抽调到来时,心情还是格外的高兴。一来总算是告别了田间劳作;二来总算学校学习的知识能派上用场;三来小学教师每月有5元生活补贴,生活当是有保障了。
到学校又是一番另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