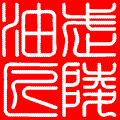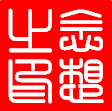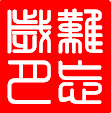难忘那次吃“斋猪肉”
初到农村,农户家庭的一曰三餐,都是队里自产的米粮和自家的蔬菜。不过年、节,不来客人是不买肉吃的。
春夏之交,阴霾天,高湿高温的桑拿天,人身上湿漉漉,倍感不适,烦。牲猪莫明其妙地死去,准是又闹瘟疫了。瘟疫,曾是无法控制的“天灾”,使人类遭受折磨已久,因而也改变过人类文明史。
有的人家猪染上瘟病,见治愈无望,首先考虑如何挽回经济损失,趁早一刀结果了它的性命,放尽污血,去市场卖掉,换回成本。
也有人抱有侥幸心理,请兽医,给牲猪打针,灌药,盼能逃过此劫。结果,头天它还能用鼻孔出气,次日就“倒板”了。人们仍会将其处理干净,与前者统称“斋猪肉” 。后者却要加上“倒板的”定语。其肉呈红黑色,腥味大,有的皮上还带有黑色的斑点。价格与前者差距较大,这下可亏大了。
人们明知食之有害,却贪图便宜,争先购之,冒险食用。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却有人津津有味地传授烹制办法,听者颇多。
一日,农机站炊事员李伯说,他们队里有未倒板的斋猪肉卖,他去买,还会给上几分面子,价格公道。邀几个人打平伙,合算。实话说,来公社菌肥厂工作,算个美差。在农机站搭伙,一日三餐不用愁,但非常单调,有白菜时节,顿顿吃白菜。有罗卜的日子,餐餐水煮罗卜片、它、块。大蒜炒辣椒,稀罕,算美味佳肴了。那时年青,称之曰:吃长饭期,喉咙深似海。数月肉未偿,日日水煮寡油多盐菜,时常口冒清水,人都变“菜虫”了,眼都放出闪闪的“绿光”。 在自己的印象中,还是过年时,在家吃团园时,饱吃过肉。其余的记忆都模糊了。确实想肉吃,又从未食用过未经检疫的猪肉。怕吃“斋猪肉”,有点迟疑,默不作声。李伯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反复讲,自己都六十出头了,不管怎样死的家禽、牲畜都吃过,身体蛮好,没因吃东西生过病。我见李伯平日待人和善,又关心知青,的确是番好意,便应允了一道打平伙。
中午,李伯端出热气腾腾,香喷喷的一大钵肉,上面盖满鲜红的干辣椒和大蒜籽,特诱人。见后,我一直吞咽口水。但还是心存疑虑,小心地用筷子夹瓣蒜籽,轻轻地放进嘴里,缓缓地嚼,不放心地咽下。
李伯见我今日如此斯文,又讲了几句,叫我放心大胆吃的话,又夹起块肥肉,噻进嘴里。其他几个伙计,头也不抬,根本没功夫搭理我,吃得挺有滋味。我心想,在不知情时,也可能真还吃过“斋猪肉” 。
今日的诱惑,再也无法使我下决心拒食这美食了。况且,此时钵中的“内容” 浅了一大节,同样出了一份银子,他们巴不得你再犹豫作壁上观。我也太亏了。打消了疑虑,也不示弱,放纵自己,同大家一道大嚼起来,美美地吃了顿“斋猪肉”。 那时确实无知,吃“斋猪肉”后,还觉得没任何不适之处,倒有过年之感。心中愉悦,特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