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个月的乡村生活,印象最深的,一是那千变万化、灿烂辉煌的晚霞。母亲几乎每天傍晚都带着我和她的一些学生出去散步。二是我们散步时要经过一所“工读”学校,黑色的大门从未见开启。我却看到学校的高墙(总有三四米吧)上常有孩子在行走!张开两手,摇摇晃晃。但他们并不逃走。母亲说,关在里面的都是一些多才多艺的少年。
六年级我又转回城里读书了。大约父母还是希望我在城里上中学吧。再则老蒋的“反攻大陆”也许只是吓唬人的。
年龄一大,脑子就有点邪,我同时暗中喜欢着不止一个小姑娘,其中最让我钟情的是学校合唱队的指挥。她比我矮一届,生得小巧玲珑,亭亭玉立,漂亮得无可挑剔。平时和女孩子挨近点我就脸红,从不敢正视。这下好了,她是指挥,就站在我们的面前。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直勾勾地盯着她看,无论她怎么挥动手臂、手腕、手指,都让我心动神移。她的目光却是虚的,把我们扫来扫去,从不聚焦。
倒不曾有过什么失落感,只是见到别的男孩和她说话时,总不免心里怅怅的。我绝不刚上前和她攀谈,也没有过与她“对眼”的美好回忆。
在合唱队我还认识了一个小男孩,白净,眉清目秀的,有种总要让人怜爱的气质。有段时间里我和他好得如胶似漆,形影不离,一天不见都想得慌(这回没有食物)。
九十年代我们再相见时,虽没多少话可说,那份亲切感尤在。
直到后来读了点弗洛伊德,才知道所有的人在少年时期几乎都会有同性恋的倾向。
这里没有初恋,自然也没有让某些师长们惊恐万状的洪水猛兽。
时光流逝,总抹不去那一片淡淡的余香。
好多年后,儿子读初三了,有一回怯怯地跟我说:“……爸爸……我交朋友了……女朋友……”我一时怔住,总有五六秒吧。
我斟词酌句,紧张得有点出汗:“你一定要尊重人家。对人家负责。要尊重人家。”
儿子懂事地点着头:“我知道。我一定。”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不再追问。儿子信任我,我就必须信任他。
但那一段日子我过得不轻松,总捏着一把汗。
至于我的儿媳妇是否那位“女朋友”,我也从没问过。
或许,事情确实就是这么简单。只是我们长大以后,常常遗忘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把原本非常简单的事,搞得复杂无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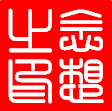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