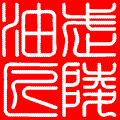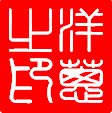“一勾”先生,家住大队部旁低矮的茅草棚内。
棚内设施简陋,值得一提的是,两张大床和床上灰黑色的被褥,泥巴糊的灶上架着口锅,一张方桌,靠壁才能保持稳定。
“一勾”先生年且四十,姓丁,几代单传,曾念过几年书,算个文化人,额如葫芦前凸,矮小诙谐,整日乐呵呵的。收工归来,连声亲热地叫喊:“俺屋里老妈子。”旁人闻之耳根发热,他却不以为然,且认为:养儿防老,娶妻生子,为传宗接代,俺屋里老妈子能多生儿子是关键,像自己独子一个,责任重大,儿子多了,东方不亮,西方亮,不必在一颗树上吊死,因而十数年如一日,仍坚持意往深情地呼唤她。
老妈子也能干,接连为“一勾”家生下八朵金花,“一勾”先生眼看过了不惑之年,心力交瘁,仍未见养出个“带把”的,倍感焦急。于是乎加班加点,不遗余力,功到自然成,屋里的老妈子又有喜了,腆着个大肚子,还在用干瘪的乳头哺乳八妹。
不久前,他偷偷请人占卦,签上讲:“九九,九九,天长地久。”这是个上上签,保佑自己的家天长地久,人丁兴旺,这回准是男孩。他笑在眉头,喜在心,情不自禁地哼起《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的选段,尽管鸭公喉咙哼得不成腔调,只要自己润味就行,别的都不在乎。样板戏中的扬子荣,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越想越兴奋。
突然一想,光顾了傻高兴,差点忘了大事,给八妹断奶,千万别影响了“九爷” 在腹中的生长发育,这可是件头等大事。可也不能太亏了这小妮子,都是她娘身上掉下来的肉,赶忙去换了几斤黄豆,和米炒熟,磨粉喂八妹。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结果大失所望,生个九妹,没把。占卦也失水准,“一勾”先生如同掉进冰窖,内外凉了。难怪这些东西算“四旧”, 近几年被批叛得体无完肤,活该倒楣。他越想越烦,终日愁容满面。
几天来,“一勾”先生不敢吱声,这事也不能全怪老妈子,她够努力的,听那当过军医的“四类份子”说:是什么X、Y的问题,不是女人的错,是老爷们的问题。这天,他在家偷偷拿了几枚用来换盐的鸡蛋,到小卖部换了几两出口转内销红薯制作的烧酒。他很少饮酒,过年节,凑兴喝一小盅,就分不清三大、还是四谁大了,想端起酒杯一醉方休,猛地喝上两大口,顿时,心跳加速,脸红,脖子粗,又喝了一大口,头晕乎乎的,趴在柜台前,将剩酒一饮而尽,舌头麻木,不听使唤,嗓门大了,乘着酒性,嚷嚷着:“谁、谁…要要是这辈子还,还打光棍……,别怪我‘一勾’了,我我这这……辈子专为光、光棍作、作……贡献,算有有有功之……臣。”
从此,“一勾”先生心灰意懒。
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他夫妇都要出工,大女儿辍学放牛,无力照顾孩子,收工归来,孩子们从各个角落钻出来,浑身尽是草屑灰土。聚拢,个个眼瞪瞪地望着爹娘,眼泪鼻涕糊得满脸都是,像画家的调色板,家务事一大堆,又没功给她们洗脸,都是邋遢像。冬天,都只能穿着空筒棉袄,老大穿小了给老二,老二穿小了给老三,一个接一个,越小穿得越破旧,小屁股露在外面冻得通红。白天,一群头发乱蓬蓬的黄毛丫头,挤在屋角晒太阳,晚上,孩子往床上一滚,“一勾” 有时去点点人头,少了谁,他自己也叫不出名来。
贫困地区,因子女多,没能力去教育,他们浑浑噩噩地长大,有的很早就辍学,素质相对要差,又无法回避家庭生活拮据的现实,只得异乡,从事简单重复的劳动,或在家乡延续祖辈“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劳耕作,解决吃穿为人生第一目标,糊里糊涂地长大、出嫁、结婚、生子……。与贫困为伴,一代代延续着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