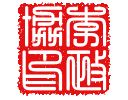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
——转载一个老知青的遗作
“×”读做叉,不能叫做字,只可以说是一个符号吧,它的起源也许和象形文字一样古老。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和这个符号结下一段不解之缘。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在“师大”当助教,正当我如醉如痴地沉湎于祖国的语言宝库之中时,忽然随着舖天盖地而来的标语和大字报,我的名字被涂上了又黑又粗的大“叉”。
从此这几个“××”就在我的心灵和生活中打上了可怕的印记,我知道这是我讲真话、讲直话和我那死也不转弯的犟脾气的报应。名字虽被枪毙,灵魂可仍在思考。生活往往从磨难中迫使你更深地想一想,同时也使你获得了咬咬牙坚持下去的力量。
一年后我被横扫到了凤岭林场二工区——莽莽群山中一个景色秀丽的小山村,这里十分偏僻,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的简易公路穿过深山老林,通向八十里外的县城。当我在这个山村里晒黑了皮肤,手上磨起一层硬茧时,又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在我的头上。起因呢,仍是那个丑陋的“×”。
我们村口有一段低矮的围墙,白粉墙底上用土红写着一副醒目的长条标语,那是当时“副统帅”的一句“名言”。不知是谁,竟在标语的第一句“读毛主席的书”的“毛主席”三个字上触目惊心地画了三把大“×”。
这桩现行反革命案立刻震动了林场,仿佛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发生了九级地震,县委和县公安局指令将这个案子列为重大案件限期侦破。人们纷纷议论、猜测,谁都感到愤慨和惊讶,在自己宁静而单纯的小小村子里,尽然隐藏着一个凶狠的敌人。
然而这个案子也有使人迷惑不解的地方:为什么在不是名字的“读”字上也画了一个明显多余“×”呢?为什么在“读”字的右下角又莫名其妙地打了一个小“×”呢?聪明老练的办案人认为,这是罪犯故意布置的疑阵,是精心设计的一个骗局。他判断这该死的罪犯文化很高,但貌似老实。
什么?“文化很高”、“貌似老实”,这是讲谁啊?在这里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讲“文化”当然数我第一,莫非……他们怀疑我?想到这个沉重的罪名,我毛骨悚然。
果然,我发现自己已成了嫌疑犯。当我经过那段围墙时,工区李支书和背着镁光照相机的公安人员正在查勘现场;一看到我,李支书向公安人员嘀咕了一句,眼光斜睨过来,还意味深长地朝我点点头;这时我脊背上“嗖”地窜过一股凉气,他那神态分明说:“啊!——是你!”
全村的人也都避开我,好像我是一个吃小孩的魔鬼,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憎恶的眼光尖利地刺过来。
然而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一位姑娘——林区的赤脚医生柳蓉。当我们迎面相遇时,我对她摇摇头,心里说:“别相信,不是我!”她懂了,停下脚步注视我,张张嘴想说什么,又忧郁地垂下眼皮走过去。另一个是柳蓉的侄子杨冀,刚刚五岁,小名叫小冀子。
那标语上的“×”没有我作案的证据,也没有不是我作案的证据,我无法为自己辩解。只有逮住这个该死的家伙,才能证实自己的无辜。
罪犯总不会自己跑出来亮相吧,更不会忽然从地下冒出个拯救我的救世主呀,唯一的办法只有“自己救自己”了!于是我趁着暂时还没有失去自由,暗暗查访。我分析观察全村每一个人;还装作到村口去打水,偷偷地到那块标语前去仔细研究“罪证”——那足以置我于死地的“×”。
我紧张地做着这一切,我有一种紧迫的预感,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什么时候就可能把我五花大绑抓起来,加上原来的“罪行”,判个十年、二十年,或者干脆一粒“黑枣”送我上西天。
我怀疑作案的是个小孩,因为只要多少读过一点书,大概很少会把“读”字认错,而那“读”字上古怪的一大一小两个“×”,实在很像出于儿童心理搞的把戏。
正当我在房中冥思苦索的时候,夕阳的最后一缕光辉射进窗子,把一个什么影子映照在墙上就像一个大大的问号。忽然,有个孩子喊了一声“猴子叔叔”,推开门轻悄悄地走了进来。这个孩子皮肤晒得黧黑,长着一头卷曲的短发,一双逗人喜爱的大眼睛——进来的正是小冀子。小冀子是我在林场的“知心朋友”。请不要笑话“知心朋友”这个字眼,一个三十岁的大学助教和五岁的孩子成了“知心朋友”,岂不荒唐吗?在那个“斗争”淹没了一切的年代里,我这个充满了惊恐和疑虑的被斗者能交朋友?但是小冀子却在我患难中送来了纯真的友谊,使我受伤的心灵得到了温暖。
是他!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像电光般一闪,打“×”的是他!是小冀子!
我把全村的人想遍了,就是没有想到他,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
小冀子看见我突然皱紧眉头苦着脸,,赶忙问我“叔叔你头痛吗?”“去,去,……”,我真像哪里痛得厉害一般,狠狠地哼了一声,连连挥着手,把莫名其妙的小冀子给打发走了。
我的答案并没有使我“解脱”,一旦认定了打“×”的是这个小家伙,我是束手无策,陷入更加难堪的境地了。咳!这个“罪犯”和他“作案”的动机,完全出乎我和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