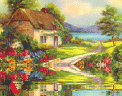又到“七月半”
[明明]
入夜,楼下鞭炮声响成一片,烛光照亮墙根。我知道,又是七月半了,街坊邻居正为故去的亲人贺节。倚窗遥望那一堆堆燃烧正旺的纸钱,我的思绪一下驶向久远的过去,回到儿时我的家。
我家曾经四代同堂:老外婆、外婆、妈妈、加上我。一代一个女子,家里没有男丁。
老外婆当年已逾古稀,却仍有一对明亮的眼睛。稍大我才知道,其实她是个睁眼瞎,什么都看不见。她常坐在一张四平八稳的方櫈上,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兼拥我入怀,哄我睡觉。那时我大约三岁,有点顽皮,时不时爬到她膝盖上,捏她松软起皱的面颊。老外婆从不生气,竟还“我的宝贝”“我的满崽崽”叫过不停。
记得老外婆用缠在腰间取暖的布带,给我做过一个有头无肢的布娃娃,并坚持说它比邻居凤妮的洋娃娃更漂亮。我相信了她,因为她是这个家的绝对权威。老外婆的权威,曾大到让幼年的母亲羡慕不已。据说某次别人问起娇嫩嫩的母亲长大想干什么时,她忽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奶声奶气回答:“我想当外婆!”小小年纪想做外婆,当场笑翻一屋人。
老外婆是五十年代走的。当时太小的我还不懂生离死别的悲伤。见大人跪在地上给老外婆磕头,我也跪下磕过不停。此举让原本轻声抽泣的外婆,终于忍不住内心的痛苦,大放悲声。
当晚,许是外婆太忙,我被送到凤妮家借宿。我挺乐意这种安排,凤妮更是欢呼雀跃。我俩是最好的朋友。钻进被窝,凤妮将她心爱的洋娃娃搁在我俩中间,我快活得有点不知所措。握住那个“乖宝宝”的小手,我决定天明后让老外婆也摸摸它,摸完她就该知道,究竟谁的娃娃更好。
这个打算自然落了空。从此我再也没见过老外婆,以及她那条腰带。许多日子后我问起才知道,七月半鬼节,外婆烧包时一并将它烧给了老外婆。说是“老祖宗在那边需要用呢!她体弱,冷不得的。”
我的外婆象她瞎子娘一样,命苦,早早做了寡妇。当年我们那个四口之家,主要靠外婆支撑。我妈纯粹一个林黛玉:美丽、柔弱、常年生病。她不仅帮不了多少忙,反给这个穷家添了许多乱。起因是“坐对花轿,嫁错郎”。
为了我们这个“母系氏族”,外婆纺纱、织布、种地、喂猪,啥活都干。每天忙里忙外活象一匹不知劳累的老马。我从未见她休息,也从没见她生病。有次我好奇的问她:“嗲嗲,妈妈老是生病,你怎么就不生病咧?”外婆听了忍不住大笑,接着“呸呸”两声说:“阿弥陀佛,童言无忌、童言无忌!蠢家伙,生病有什么好?你还希望我生病呀!”我很认真地回答:“病了就能休息,就可以睡懒觉。我就是要你生病嘛!”听我这么说,外婆显得有些惊讶。随后她含笑说:“我的儿,你长大了,晓得心疼外婆了。多谢你的好意!可是我的心肝宝贝,嗲嗲有太多事要做,没时间生病呢!”
外婆说得不假,上有老下有小的她,真的没有时间生病。她坚持、坚持、再坚持,直坚持到我参加工作,才轰然倒下,一病不起。
外婆是得心脏病去世的。
我陪外婆走过最后一段时光,却没能为她送终。借古人一句话,是“忠孝难两全”。当时探病假已到,我不得不启程回单位。想不到我还在返疆途中,外婆竟永远走了,她再也不能兑现“秋天红枣下来,我多买些,蒸熟,去皮,洒上白沙糖晒干,给你寄到新疆去”的承诺。
对外婆的离去,妈妈和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好多年都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一个一辈子不生病、一辈子没时间生病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她真的精疲力竭不得不放弃她女儿国里的儿孙了?!
……。
我是在外婆爱的摇篮里长大的。她的爱有如一道暖流,年复一年,缓缓流向我的心田,叫我刻骨铭心。现如今我已为人之祖当了外婆,却依然会在梦中,孩子般焦急的寻觅我的“嗲嗲”。
无法形容我失去外婆的悲痛,然而比我更伤心难过的是孤独的妈妈。
自从我少小离乡,远赴边疆谋生,家里就剩妈与外婆相依为命。弱不禁风,一贯倍受家人重点保护的她,突然没了母亲,觉得塌了整个天。她对着日记发出“前无杀将,后无救兵”的哀叹,字里行间,泪痕斑斑。
六十四岁那年,母亲与世长辞。
母亲的一生,是充满坎坷,不幸至极的一生。她饱受病魔和强权的双重摧残。我不想过多回忆母亲长达四十年,受尽苦难屈辱的种种往事。因为一想到她高烧不退,还必须挣扎着在烈日下砸石修路;一想起她娇美瘦弱的身躯,被政治歹徒打翻在地,倒拖着游街示众;白发外婆拼死救援无果,倒地嚎啕大哭的惨状,数十年过去,我的心依旧痛,心酸的泪依旧流!善良的母亲做错了什么?她工作勤恳、为人正派、低调生存。唯一做错的就是嫁了不该嫁的人!父亲谋生去台湾,成为她厄运的开始、终生躲不开的祸根。
啊,我可怜的娘亲!
窗外,鞭炮还在噼呖叭啦炸响。一年一度七月半,今年我拿什么祭奠我逝去的亲人?灵屋纸马、百吨冥钱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依恋;千言万语、锦绣文章寄托不了我对你们的哀思!呜乎!阴阳两隔,再难回报。祝愿你们在天堂过得无忧无虑、尊贵富足;一百年后,但愿我们祖孙几个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