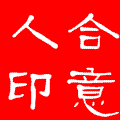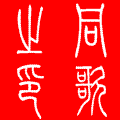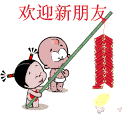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报名下放安乡了。逢事并无主见的我,这次却没有随大流,而是瞒着父母,悄悄的将户口迁至耒阳.其原因之一是:到耒阳考察回校的某老师说:耒阳是个好地方,板栗铺路.我便奔板栗去了。
下放后,便多方查证:我下放的这个乡根本不产板栗.即便是耒阳县也不以产板栗著名。失落的心又平添了一份怨恨.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次年,我没见板栗,却见到另一种丰收景象。那便是油茶成熟时满山的油茶籽,不但晒谷坪铺满了,山间小路屋前屋后的空坪隙地都铺满了茶籽。原来,到耒阳考察的某老师,系城里生,城里长,也不分清板栗和茶籽.被骗的感觉释然.倒是觉得比那位老师要多晓得一些东西。
茶籽晒干去粗壳后,却要开榨,知青便被派去榨房出公差。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浩浩荡荡的一行人一人挑一担茶籽到榨房,只见几位彪悍的男人,赤裸着上身,一人穿一条过膝的短裤。据说,这是因为有女知青到,公社特意通知他们着装的。不然穿得还要少。队上送的茶籽多,我被派去做中饭,燃料是茶籽壳。主菜是两只活鸭,一捆青菜。我到塘边,杀鸭,洗菜,淘米。并特意将知青们带着路上当水果吃的硬土里长的红薯,洗了七、八个,准备和米一起煮。当一锅红薯米饭闷熟后,我便将它们盛到一个木桶里(因为只有一个锅)。盛饭时,那带着一层薄薄的金黄色锅巴的饭,散发出一阵阵香气。那香中还夹着一丝丝红薯的甜味。
洗干净锅,拨开灶火,我开始烧菜。先到榨房里搯一大勺刚榨出来还有一定温度的茶油倒入锅中,待油温升高后,先放一大把干辣椒和适量的大颗粒海盐。待到与干辣椒炸出香味后,再将剁成大块的鸭肉放入锅中一起炸.当透过蒙蒙水雾看到鸭肉皮微微卷起后,用几勺乡里自制的豆瓣酱,搯一大瓢清澈的井水一起倒入锅中焖,鸭肉酥软后,又改为小火(即将茶籽壳盖好火)再焖几分钟.做两大盆装了。炒小菜,那自是行家里手.至于是哪种青菜,还在当知青时便已忘记。现在更想不起来.只依稀记得,由于火大,油多,那炒出来的小菜表面似乎涂上了一层透明的汁液.鲜嫩的碧绿色更胜缅甸产的翠玉。吃饭时,我没听见榨房里师傅们讲话,也没听见知青们交流,也没听见贫下中农“策”长沙人,只听见舌头搅拌着牙齿,上唇击打下唇。待大家将一切(包括鸭骨头)扫荡完毕后,我闷头收拾碗、筷。这时,大概是榨房里一位负责的农民用学会不久的长沙话说:咯个城里妹子不错,做事利索,手艺蛮好。明天他们队里送茶籽来,还派她做饭。至此,我那颗悬着的、不愿在众人面前显摆的心才平稳的放在它应该呆的位置。
现在,本人添为家庭主妇,职掌锅碗瓢勺,也从来没有把煮饭烧菜当成负担。但是,我再也没闻过榨房里的那种饭菜香,也很难感受到表扬我厨艺好的受用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