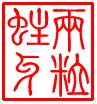(二)
松桂园历险使我等三小子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次日在年嘉湖畔举行了三人会议,谋划星期天到建设电影院的巷子口上摆图书—小人书摊 。
那天早早的,我们扛着帐竹竿、麻绳和自己凑合起来的36本小人书,还有几张竹椅子,悄悄离家来到建设电影院的巷子口,七手八脚地扎起图书书架。三横长,两竖短,斜靠墙边,活脱脱老书先生子曰诗云地摇晃出的那个颇像孔夫子脸面的“曰”字。胡乱横牵在架子上的几根麻绳和与书架容量太不成比例的孤零零的几本图书,充其量只是孔夫子那张“曰”字脸面上的几道皱纹和参差不齐的须毛。
到了快吃中饭的时候,未有分文进帐。三小子吵了起来。才子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准备撤资,说是至少带走他的《少年文艺》和《三国演义》第一册《桃源结义》,要不然爸爸会打他。混小子先是左倾盲动主义,要揍才子,并且,强行宰客,扭住一小孩:“你翻了图书,又不看,也要给钱。”才子刚刚走,混小子又犯了右倾逃跑主义,说是没有味,他要回去吃饭了,图书和架子他不要了,再也不来了。被他们严厉批评只晓得自己看图书,又不管事的我,憨憨地剩在那里,望着书架和图书还有几张竹椅子发呆。
下午,妈妈接到混小子线报来接我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两分钱进帐。一个同样懵懂的小女孩带着一个比她更懵懂的小女孩,说是她只有两分钱,想两个人各看两本厚的外加一本薄的。我说随你看好多。
妈妈这一盘算,在这里摆图书,投资回报率不会低,也没有责怪我,当即拍板斥资6块,做大做强。并且,决定从下周起,星期天白天我守摊,其他时间我的妹妹还有她自己有空,都要轮班。
我的图书摊迅速红火起来。尽管被孔乙己们窃书的事是时常发生的,才子和混小子作为书摊贵宾,看书是不用付费的,妈妈也没有指责我。妈妈认一个死理,孩子爱看书是好事,况且,这书摊是孩子亲自创建和发展来的,一切的听从孩子的指挥是理所当然的。
到文革“破四旧”的时候,我的书摊各种图书被打捆,“藏”书已达两千多本
(三)
建设电影院的放映厅隐在一条叫顺心桥的大巷深处。记得前厅里挂有赵丹、张瑞芳、白杨、秦怡、舒绣文、孙道临等等“天王”级影星真诚清纯的单人照。一般,那儿不是我们这些小子们常去得起的殿堂。
电影院售票厅在巷子口的一侧,面对车水马龙的马路。巷子口的另一侧熙熙攘攘的,墙边就是我的图书摊。常常看得到,一些青年哥哥唉声叹气地问我有没有票卖,星期天我又干起倒票的第二职业来了。不过,这营生一直不敢让妈妈知道,也没有做多久。售票厅开门,我还没有开架上书,就去买票,好像一次最多也可买5张票。到电影快开映,临场买不到电影票的青年哥哥们,有的看着噘嘴的女友,急得摇着售票窗只跳。我便诡秘地掏出票来一晃,大人们就洋葱皮一样一层层拥挤在我周围放抢,大喊;“我出一角”“我出一角二”,“一角五”而且,哪位文雅君子、冷艳姐姐对我稍有不恭,比如叫我小屁股——那可是汉子叫的,岂是你等书生叫得的,我就扳翘“不卖”。回想起来,成就感不亚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印象中,放映《抢新郎》、《 乔老爷上轿》八分钱一张的票最高卖到过一角五,几乎一个涨停板,至今我对钱塘县那位艳福不浅的秀才,及满城的拉婿傻女,还有乔老爷都心存感激。
那次我高价抛出最后一张票,从人堆里钻出来的时候,一头撞到一个没有挤进人墙的男子身上。抬头一看,是我的老师, 一个油亮小分头的严厉小生。我诚惶诚恐叫了一声,“老师。”他一看刚才不给他面子的竟然是我:“你,你搞投机倒把。” 我慌不择言:“老师再见。”说着,把留给自己的一张票塞给了老师,拔腿便逃。
我其实是怕事的小子。一怕老师抖露给学校,吃不了兜着走;二是怕老师到妈妈那儿告状,妈妈饶不了我。到了后来,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第二天老师把票钱不动声色地还给了我。此后,我也金盆洗手了。
至今,我还不明白,我给老师塞票的潜意识动机是敬畏,是贿赂,还是像章鱼和别的什么逃生动物一样放一股墨汁、丢一个嗤屁就逃,或者兼而有之。